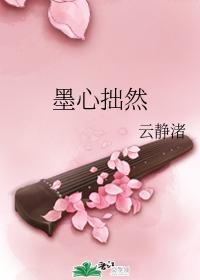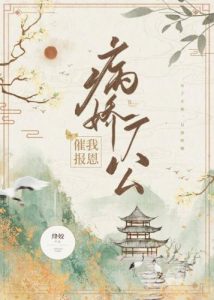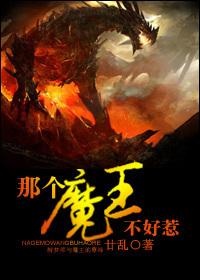第 71 章
吃過晚飯後, 許大郎夫妻兩個沒有像往常一樣去食肆準備明天的菜品,而是端了碗炒豆子回到屋裏,商量起了謝虞琛今晚說的話。
餘娘子和許大郎夫妻兩個一人一把炒熟的豆子, 嚼的嘎嘣作響, 但都不說話, 像是在等對方先開口。
至于一旁的餘小郎,他倒是想說幾句, 但這個時候顯然沒有沒有他說話的機會。
最後還是許大郎把手裏抓着的豆子放回碗中, 嘆一口氣,開口打破了屋裏沉默的氣氛:“謝郎是為咱們家小郎好,才跟咱們掏心掏肺地說這些。”
謝虞琛方才在飯桌上說的話,都是實實在在的,在幫許大郎夫妻兩個分析利弊。餘娘子當然清楚這一點, 知道謝虞琛說的那些話都是為了餘小郎好。
如果不是真心為餘小郎的将來打算, 誰會冒着得罪人的風險說那些。而且不管怎麽看, 謝虞琛都不像是那種愛多管閑事的人。
她把手搭在大腿上, 輕輕點了點頭:“謝郎是為了咱好,我當然知道。我就是知道謝郎說的都是真話, 這心裏才難受啊。”
自她姊弟二人的爺娘過世後,她倆相依為命,咬着牙熬的那種苦日子沒少過。
後來嫁給許大郎,他們夫妻二人感情和睦,對于餘小郎這個她帶過來的小弟, 許大郎也從沒表現出一點嫌棄。甚至比尋常人家對自己的親生孩子還要寬和。
對于現在的日子,餘娘子已經很滿意了。她現在只想着跟許大郎一起把食肆的生意經營起來。至于更高遠的事情, 餘娘子是從來沒有幻想過的。
一家人能和和美美的過日子,已經是許多人不敢奢望的事。能有現在的生活, 餘娘子是打心眼裏的滿意。
對于餘小郎,她也從來沒有讓他做官入仕、光耀門楣之類的打算。或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她也曾幻想過幾回。但這些離他們普通人都太遠了,人還是要腳踏實地的才行。
抛開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餘娘子之前只想讓小郎學一門能夠糊口的手藝。等他長大之後,自己再給他說個好人家。她也就算是對得起自己過世的爺娘了。
是謝虞琛的到來,才讓餘娘子有了一些想望。謝郎說餘小郎天資聰穎,知識學得很快;謝郎還說餘小郎的領悟能力也很不錯……
誰能不想讓自家孩子能有出息呢?
“能跟在謝郎身邊學習,是多少人求都求不來的好事。”許大郎拍了怕餘娘子的肩膀,寬慰道。
他知道,餘娘子是舍不得餘小郎小小年紀就要離家去那麽遠的地方。但若是因為舍不得,就生生錯過了這樣的機會,将來怕是少不了要後悔的。
過了好一陣,餘娘子才擡起頭,輕輕擦拭掉眼角的濕潤,點頭道:“你說的對,能跟在謝郎身邊學習,是咱們的福氣。”
心中搖擺不定的天平終于朝某個方向滑去。餘娘子朝默默拎了個板凳坐在角落裏的餘小郎招了招手,示意他過來。
四目相對,餘娘子問道:“小郎你想清楚了嗎?願不願意跟在謝郎身邊?”
餘小郎低頭,手指有些不安地攪着,許久才點了點頭,聲音微不可察:“我願意的。”
餘娘子和徐大林對視一眼,終于做了這個決定:“只要你願意就行。那阿姊就去給你收拾行李了。”
她原本打算起身出門,但走出兩步後,又像是想起什麽似的轉身回來,輕輕把餘小郎攬進了自己懷裏。
……
既然要跟謝虞琛一起離開,又是那麽長的一段路程,出發前的準備是肯定少不了的。
這幾天許大郎和餘娘子兩人基本把食肆的事情都放在了腦後,一心一意地為餘小郎置辦起路上要用的東西來。從鋪蓋再到衣裳,零零碎碎準備了一大堆,生怕他帶得不夠周全。
謝虞琛那邊自然也沒有閑着。第二日剛吃過早飯,他便帶着田福替自己雇來的工匠到了作坊。
首先要做的就是跟他們簽訂合同。至于培訓什麽的,就交給作坊裏的其他人先帶着。只是制作香皂的話,其實并不複雜。
不過是将各種原料按照比例混合攪拌,最後倒入模具中冷卻凝固這幾個固定的流程。只要掌握了幾種原材料的配比,基本就沒什麽大問題了。
非要再說一點的話,那就是需要對皂液的溫度熟悉一點。這個年代沒有溫度計,什麽溫度适合裝模都是憑借工匠的經驗和手感。
但這些也都是只要多練就能掌握的技術,對工匠來說并沒有多少難度。唯一需要謝虞琛發愁的,大概就只有工匠來了作坊之後,原有的住處變得有些緊張。
原本謝虞琛計劃的是,在今年春天大家夥忙完地裏的事情後,就雇幾個人把現有的作坊擴建一下。
作坊現在占的院子原本是租的一戶人家閑置的院落。後來香皂生意穩定之後,謝虞琛在修建新廠房和買下這座院落之間糾結了幾天,最後還是為了省事選了後者。
凡是蓬柳村人,基本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受過謝虞琛的恩惠,這間院子的主人也不例外。既然是承了人家的情,那自然要回報。
這間院子的主人聽說謝虞琛打算買下他的院落後,幾乎沒怎麽猶豫便答應了下來。
二人請了裏正做見證人,簽訂了合約,一式兩份。謝虞琛便以一個很實在的價格把這間院子給買了下來。
拿下這間院子之後,謝虞琛就把擴建給提上了日程。本來就不大的地方,硬是塞進去三架蒸餾器皿、一排加熱皂液的竈臺。還要空出一間房堆放收來的花瓣,一間房儲存需要繼續皂化的香皂半成品和香水。
最後僅剩下三間偏房,做了工匠們的“宿舍”。
原本就已經滿滿當當的,現在又多了二十來個工匠。別說是住處,就連做工的地方,怕都是騰不出幾塊了。
看着連在裏面轉身都很困難的作坊,謝虞琛捏了捏鼻梁,許久才一臉牙疼地把常三叫回來。
就在前幾分鐘,謝虞琛才吩咐了常三,讓他帶着新來的匠人熟悉熟悉地方,跟在老工匠身邊學習香皂的制法。
“謝郎您叫我可是有什麽事?”常三小跑兩步,在謝虞琛身前站定。
“先把那些人叫回來吧。”謝虞琛無奈扶額:“這幾天就先不用讓他們練手了。”
果然,聽到這話的常三一臉問號地“啊?”了一聲,雖然沒有開口,但謝虞琛已經能感受到他的疑惑了。
“沒別的原因……主要是咱們作坊,容納不下這麽多人了。”
“原來是這樣。”常三尴尬地笑了笑。
但顯然,在場有一個人比他還尴尬。吩咐了幾句後,謝虞琛便火速離開了作坊。
出了作坊的大門,沒走幾步路,就迎面遇上了幾個追着玩鬧的小孩。
幾個小蘿蔔頭見到謝虞琛,連忙停下了腳步,面上帶着笑,站在原地挨個向他問好。
蓬柳村裏的小孩基本都聽過謝虞琛的名字,即使他們家裏沒人在許家幹活,但也都跟着大人來食肆打過醬油、買過吃食。
不過村裏的孩子都不怎麽怕他,每次見到謝虞琛時,基本都是笑嘻嘻的。有幾個膽子大的甚至還會主動湊上來跟他搭讪。
小孩雖不像大人那樣懂得人情世故,但在某些方面,他們是很敏感的。大人是什麽樣的言行,小孩子們也會模仿學了去。
村裏的百姓對謝虞琛的态度都是感激中帶着幾分尊敬。這種态度會滲透到他們平日裏的一言一行中。身邊的小孩跟在大人身邊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對謝虞琛也會抱有相類似的态度。
謝虞琛看這些小孩也都有意思得很,每次遇上他們時,都會停下來笑眯眯地跟他們說幾句話。若是離得食肆不遠,他還會請他們吃一些甜點。
這些“糖衣炮彈”很快便俘獲了村裏孩子們的喜愛。如果讓村裏的小孩評選出一個他們最喜歡的人,謝虞琛一定會毫不意外地獲選。
謝虞琛剛一招手,幾個小孩便呼啦啦地跑過來,把他嚴嚴實實地圍了一圈,七嘴八舌地“謝郎,謝郎”叫着。
謝虞琛拍了拍其中一個個頭最高的小孩,然後開口道:“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們幫忙,不知道你們願不願意啊?”
聽幾個孩子齊聲聲地答了一句“願意”,謝虞琛笑了一下道:“你們幫我去王大嫂家,給他們家二郎傳個消息,就說是我找他有點事情,讓他若是有空,就來食肆一趟。”
他話剛一落音,還沒來得及問一句“記住了嗎”,面前的幾個小孩嘩啦啦便跑了個沒影。只留下謝虞琛一人站在原地,無奈地搖了搖頭,轉身向食肆走去。
“聽說謝郎找我。”王家二郎一聽是謝虞琛找他,放下手中的活計便跑來了。
“快進來說,外面還冷得很呢。”謝虞琛一撩門簾,趕緊把王二郎招呼進來。
兩人坐在榻上,手裏各捧着一碗熱茶。
“你還記不記得去年建立的施工隊?”謝虞琛開口問道。
去年春天的時候,石灰砂漿在江安府小火了一把,許多人家都買了石灰和細沙翻新院子。因為這個法子是從他這兒傳出去的。因此人們在雇傭工匠時,都更偏好雇他們蓬柳村出來的男郎。
當初擴建許家食肆的那些人,後來便在謝虞琛的指導下成立了一個類似施工隊的群體,跑去各地給人家刷牆打灰,也賺了不少銀錢。
這個施工隊的領頭,便是王家兄弟二人。這門生意火了好幾個月,連帶着王家兄弟也在外面有了些名聲。
後來請他們翻新院子的人越來越少,畢竟能承擔得起石灰昂貴的運輸費的人家還是少數。他們一行人便又結伴回了蓬柳村。
現在謝虞琛提起施工隊的事情,王二郎趕忙點頭道:“我當然是記得的。”
見王二郎神情嚴肅,謝虞琛露出一個溫和的笑容,“我打算這幾天把香皂作坊給擴建一下,想着你們在這方面應該更熟練些,便把你叫過來,問問你們有沒有空做這個營生。”
畢竟他們是合作過的,對彼此也更熟悉,所以謝虞琛這回還是想優先雇傭他們。如果王二郎等人沒空,他再去找其他人。
謝虞琛有活能先想着他們,王二郎自然是很高興的,連忙應聲道:“我們兄弟二人肯定有空。其他人我回去之後便替謝郎問問。”
“那便有勞了。”謝虞琛點了點頭。
主要是作坊擴建的事比較着急,施工隊的人又都是參與過許家食肆修建的,對他的要求,還有各種圖紙都比較熟悉。
如果施工隊沒有空,他再去其他地方招一批人,難免要浪費幾天時間。好在施工隊的小夥子們一聽是謝虞琛這邊要用人,當即便帶着工具趕過來了。
第二天,作坊衆人把裏面的東西騰出來之後,便開始了緊鑼密鼓地趕工。
這段時間,田福帶來的幫工都被謝虞琛安排到了村人們打掃出來租用給行商的屋舍中,吃住都從他自己賬上扣。而白天呢,就在作坊裏做些搬東西的雜活。
像他這樣雇了工人之後自己先花出一筆錢的,也是不常見。
也得虧是這段時間大家都忙着農事,來往于蓬柳村的商販也少了些,村裏才能空出不少屋舍來。若是碰上村裏最熱鬧的時候,還真不一定有那麽多的地方給這些工匠。
作坊這邊忙着擴建,謝虞琛也沒閑着。這幾天他光是拿着賬本一筆一筆地算賬,就算得頭昏腦漲的。更別提旁邊還杵着一個常三要教。
他這回離開蓬柳村将近一年的時間,香皂作坊肯定要安排個靠譜可信的人接手。許大郎現在光是忙食肆的事情,就已經是精疲力盡,根本不可能再兼顧作坊的經營。
而且以許大郎老實巴交的性格,也并不适合和那些商販們打交道。謝虞琛物色了半個來月,最後從作坊的一衆工匠中選了常三出來。
常三這個人吧,能力肯定是有的。一場時疫下來,能成功逃到其他地方的都是少數中的少數。更不用說這一路上還要經歷無數坎坷。
根據謝虞琛這段時間的觀察,常三在各個方面也都比較符合自己的要求。更關鍵的是,他的妻兒也都在身邊,之後也有很大概率會在蓬柳村安家。
唯一一點不合适的地方,大概就是常三這人的數學水平一般,尋常算個幾十文以內的帳還行,但遇上賬本上的這種大額的數字,就有些傻眼了。
不過也能理解,這個時代的普通人家大多都沒有機會接觸書本和知識。數學在這個年代也不容易上手。
所以除了那些商販貨郎以外,大部分普通的人的數學水平,還真抵不上後世小學一年級的小朋友。
不過還好謝虞琛有當初住在寶津渡的時候,教茶樓裏的衆人算數的經驗,現在遇上常三也不算無從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