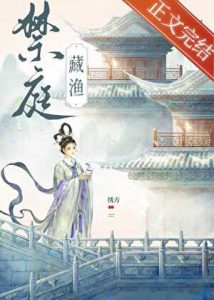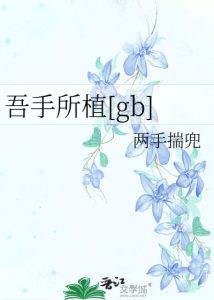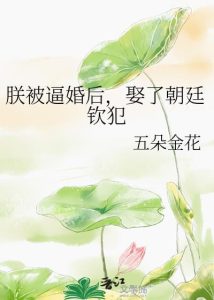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83 章
一行人到了東山州的時候, 太陽已經落山。
謝虞琛的住處還是他上回住的地方,只不過上一回是以烏菏的身份出現,這一次用的他自己的模樣。
長史将謝虞琛一行引進院中時, 心中還納罕, 想着這位郎君明明是第一次來, 怎麽好像很熟悉這院子似的。不過這點疑問在心中想想就行,若要讓他問出口, 他還沒這個膽量。
這位可是奉了巫神大人的命令來他們東山州的。沒看到就連他的頂頭上司的關大人, 一州刺史,都對這位身份神秘的郎君一副畢恭畢敬的态度嗎?
他一個小小的長史,撐死了也就是個正六品的小官,放那些大人物跟前提鞋都不夠格,人家是什麽身份哪輪得着他來說三道四。
他聽同僚們私底下議論, 跟在這位謝姓郎君身邊的年輕人, 就是那個穿着圓領的大袖長衫, 衣袍寬大, 一看就是那種出身很不錯的世家子弟,居然是沈家現任家主沈望的次子沈元化。
今天他去迎接幾人的時候, 分明聽到另一人稱呼沈元化為“沈兄”。但看兩人相處時的神态,他反倒覺得是沈家的這位要更殷勤些。說話時也是沈家郎君湊到另一位公子身前去說。
長史心中訝異,要知道沈元化可是沈家嫡出一支。出身沈家那樣的大家族,就算是直接去掌一州之治都不過分。他實在是猜不出到底是什麽樣的身份,才能讓沈家二郎這種人都推崇得不得了。
想來應該是什麽不可多得的人才罷。長史心道。
也不知道他們東山州是撞了什麽大運, 去年差不多也是現在這個時候,迎來了代天子出巡的大巫。不僅帶他們建了采石場和水泥作坊, 還出手整治了欺壓百姓的仲學文一流。今年眼看又迎來了一位貴人。
去年這個時候東山州發生了水患,但因為有巫神大人在, 甭管是治理水患的官府,還是調度赈災糧款的那些人,都兢兢業業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不敢有半點差錯。
采石場現在已經成了東山州最賺錢的地方,州府的財政也因為水泥的生意沒原本那麽緊縮了。不僅如此,去年開辟的那千畝杜仲林更是讓許多災民都有了一份維持生計的活計。
這幾天關泰初命采石場開始采摘杜仲葉,又需要一大批的人手,不僅是州裏的人,就連臨近幾個村縣的百姓都聞風而動,帶着幹糧和工具趕到了杜仲林區。
不知道這位身份神秘的郎君又會給他們東山州帶來怎樣的機遇。
***
“林場那邊已經不怎麽缺人手了,但我看每天新來的百姓還有不少,不知道是否需要派人通知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關泰初就在林場的幾個管事的跟随下來拜見了謝虞琛,向他詢問起杜仲林的事。
闊別将近一年,謝虞琛再見到關泰初,對方和他記憶中的模樣倒是并沒有太大差別,就是稍微胖了點。
不知道是不是經常在府衙和幾個采石場、林場之間奔波的原因,原本那個瘦瘦幹幹的老頭好像又黑了一點。若不是身上的那身官府,根本看不出來是一州刺史。
“先不必驅趕他們。”謝虞琛搖了搖頭,“除了采摘杜仲葉,杜仲膠制取還要用到不少人手。”
關泰初應了一聲,又帶着點小心翼翼地試探問:“不知謝郎所說的制取杜仲膠,大抵需要多少銀錢呢?”
“東山州的狀況……郎君大抵是知道的,州庫裏的銀錢實在是不太充裕。”關泰初有些羞愧地解釋道。
“不是有了采石場的進項嗎?”謝虞琛疑惑地蹙眉:“州府的財政竟沒有好一些?”
“自然是有的。”關泰初連忙解釋:“是因為今年開春的時候,州府組織人鋪了幾條水泥路,然後在城外修建了一處防洪的堤壩,又挖了一道水渠。這才……”
謝虞琛無奈地擺了擺手,他算是明白為什麽把水泥這麽賺錢的生意給了東山州,官府還是一副緊巴巴的模樣了。敢情州府和一夜暴富的那種人一樣,驟然富裕起來,開始了報複性消費。
好在官府的錢都花在了該做的事上,沒有被浪費。這也是唯一讓謝虞琛比較欣慰的地方了。
不過關泰初雖然這麽說,但報給謝虞琛的那個數字還不算太離譜,起碼沒有到讓他頭疼的地步。
謝虞琛大致估算了一下,若只是修一道引水的水渠,再修幾個發酵用的水池,應該還是綽綽有餘的。但想大規模地提煉杜仲膠,恐怕就有點難度了。
不過只要能先提煉出一批杜仲膠來打開市場,以杜仲膠的實用性,不怕日後沒有收益。
“之前吩咐給……”謝虞琛有些生硬地停頓了半瞬,才又開口道:“之前應該有讓你們建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挖發酵池?”
“您是說用水泥抹面的那種四方池子嗎?”旁邊一人張開胳膊比劃了一下,見謝虞琛點頭,連忙道:“有的有的。都按照巫神大人的吩咐建好了。”
“那就好,待會兒帶我過去看看。”謝虞琛心裏盤算了一下,發酵池若是建得可以,又能省一筆錢出來。
但等到了發酵池的地方,謝虞琛才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就是發酵池雖然按着他的吩咐建在了靠近水源的地方,但取水依然是個難題。
在謝虞琛的印象裏,能夠從杜仲樹中提取出膠質的方法倒是不少,但在這個時代基本不具備可操作性。唯二能用的辦法大概就只有堿浸法和發酵法了。
這兩種方法無論是哪一個,都需要用水來洗去原料中的雜質,才能得到裏面的膠體。以他們現在一千畝杜仲林的生産規模來算,需要用到的水量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不過謝虞琛考察了一下周圍的環境,發現把發酵池建得這麽高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東山州每年雨季的時候,河裏水量都要暴增,有些河段水位升高個幾米都是常态了。為了不被暴漲的水位淹沒,工匠們也只能把發酵池挖在比較高的地方。
“這樣吧,”謝虞琛想了想,指着距離發酵池不遠的地方吩咐身後的人:“你看能不能在這兒修建一道水渠,把河裏的水引到發酵池附近來。”
長史皺着眉琢磨了一會兒後為難地開口道:“怕是有些難度,這邊的地勢還是高了些,想要從下面引水不是件容易的事。”
衆人的臉色一時間都有些難看。好不容易修的發酵池,竟然不能用?這可讓他們找誰說理去?雖然水泥用的是自家作坊裏産的,但也是真金白銀的東西,浪費也不是這麽個浪費法。
見衆人神情懊喪,謝虞琛嘆了口氣,寬慰道:“這事留給我來想辦法吧。”
正好他前些日子在琢磨筒車的原理,若是能成功造出筒車來,眼下的困境便能迎刃而解了。
筒車最大的作用便是能把流水從低處運往高處。在坡地上按照高低修幾階水渠,中間通過筒車相連,便能把低處河流中的水運到現在發酵池附近。
而且因為東山州多山,水流比較湍急,帶動一架筒車轉動也是綽綽有餘。
“你們當中可有誰是懂木工技藝的?”
謝虞琛的目光在幾人中來回掃視了一圈,人群中有人弱弱地舉起手道:“回大人的話,小人家中是做木工的。”
“那正好,待會兒你跟我回去,我有問題要請教你。”謝虞琛笑着說道:“我做了一個木質的模型,但不知道哪裏出了問題,到時候你幫我看看。”
“不敢不敢。”男人連連擺手。
“你叫什麽名字?”
男人有些結巴地回道:“小人姓徐,單名一個壽,家中排行老三,大人喚我徐三就行。”
謝虞琛沒聽清楚他說的是上聲“許”還是陽平“徐”,又重複了一遍道:“姓許?還是徐?”
“回大人,是徐。”徐三忙回答道。
謝虞琛“噢”了一聲,又道:“若是姓許,倒是我熟知的一個人是同一個姓氏了。”他記得許大郎原本也不是蓬柳村本地人來着。
大概是這番話拉近了二人之間的距離,徐三對謝虞琛也沒有那麽畏懼了,大着膽子向他打聽起那所謂的模型到底是個什麽東西。
謝虞琛一邊帶着人往回走,一邊跟徐三解釋了一下筒車的工作原理。
迷迷糊糊地聽完,徐三忍不住感嘆道:“大人真是巧思啊。”
他心想,也不知道這位大人是如何想到這麽精妙的設計。明明原理也不是多複雜,但讓他想,他怕是幾輩子也想不出來。
在榆林的時候,謝虞琛就研究了好些時日,連筒車的模型都做了整整一排,可最後還是沒解決掉筒車排水不足的問題。
但他始終覺得自己現在的路子,大致方向是沒問題的。可能只是作為外行人的自己在一些細節上把握還不夠精确。只要來一個專業人士指導改進一下,應該不難成功。
若是在後世那個信息過載的時代,只要上網一搜,想要的知識便會奔湧而出。哪怕是對木工活一竅不通,也不妨礙他在經過網上學習後成為一個合格的木匠。
但在這個時代,若是沒些門路,別說精通了,就是入門都很難。不論是木工還是什麽別的手藝,這都是人家吃飯的本事,若是教別人學了去,那不是自己砸了自己的飯碗嗎?
眼看着徐三跟着前面的年輕郎君回了城裏,剩餘的這些人中有不少都露出了羨慕的神色。
“哎,你說怎麽就讓他徐木匠給撞上了。”其中一人有些酸溜溜地開口。
“徐老三入了貴人的眼,以後怕是要青雲直上啦!”
“沒辦法,誰讓人家運氣好呢。劉大你要是羨慕,你也做木匠去!”另一人打趣道。
“那我還會打鐵呢,也不比他徐三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