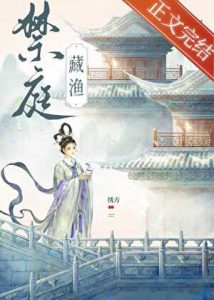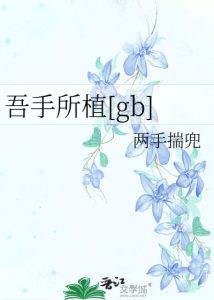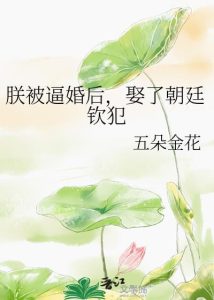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90 章
烏菏挑了挑眉, 随口答道:“放長線釣大魚?”
謝虞琛笑着點頭。林場裏的謠言能在這短短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就傳得滿天飛,說背後沒有人在暗中操作他是不信的。
于是謝虞琛想了這麽個法子,通過一筆數額不菲的獎金的誘惑, 再加上派去的兩個信得過的管事, 順騰摸瓜去探查, 果然發現前幾天的是有人故意在人群中散播謠言。
而至于為什麽不直接把這些人抓出來逼問幕後的指使者,一來是因為此事還沒有在林場造成特別大的影響。即使找到了幕後主使, 僅憑一條“散播謠言、鼓動人心”的罪名, 最多只能把那幾個散播謠言的人辭退。最後不僅不可能讓幕後主使有什麽實質性的懲罰。反而會打草驚蛇,得不償失。所以烏菏剛剛才會說要“放長線釣大魚”。
而除了烏菏說的那個原因以外,謝虞琛還有一點更深層次的算計。那就是現在的杜仲膠才剛開始生産,不僅是那些世家大族、朝中官員不清楚杜仲膠的價值。就連林場在不同流水線上工作的工匠,天天跟杜仲膠打交道, 也大多不清楚自己做的事是有什麽價值的。
這個節點絕不是謝虞琛把有人散播謠言擾亂林場秩序的事揭露出來的時候。當然, 他完全可以借烏菏的力去懲治對方。在南诏不畏懼烏菏的權勢和威名的人寥寥無幾。但這樣做勢必會讓人們覺得烏菏是在以權壓人、橫行霸道。
況且烏菏的名聲好不容易因為去年治理東山州水患有了一點轉好的趨勢, 再因為這件事背上罵名, 着實不是謝虞琛想要看到的畫面。
而等到杜仲膠面世,世人看到它的價值後這件事便完全不同了。到那個時候別說是謝虞琛想要幕後主使受到懲罰, 即使他什麽都不做,恐怕朝廷也會主動護着林場。
說到底,現在的當務之急還是趕緊讓杜仲膠大規模開始生産。不過現在他們已經掌握了杜仲膠硫化的具體可行的方法,等到實驗室的幾個小吏把這個方法教會給負責這一步驟的工匠後,便能正式開始杜仲膠的生産了。
前幾天謝虞琛一心研究如何給像塑料一樣僵硬的杜仲膠賦予彈性的時候, 林場那邊生産的一道道工序也沒閑着,按照流程生産出了幾十斤杜仲膠, 按照謝虞琛的吩咐将其貯存在了水池裏,每天還有專人負責換水。
掌握了硫化的步驟後, 首要的就是将這批杜仲膠加工成可以使用的熟膠。謝虞琛現在想到的硫化方法還是最原始的那個,就是在杜仲膠中加入硫磺與生膠混煉,通過高溫讓生膠産生硫化反應,制成熟膠産品。
但這個加熱的過程是非常漫長的。經過謝虞琛和幾個助手的反複試驗,确認杜仲膠和硫磺一起加熱,九到十個小時之後,杜仲膠才會産生彈性。
不過他們現在也沒有什麽更好的辦法了。謝虞琛倒是知道後世的橡膠硫化并不需要這麽長的時間,應該是還添加了什麽助劑。
但具體是什麽助劑、需要什麽步驟,這些就是謝虞琛不知道的了。因此他們現在采用的就是最原始的硫化方法,雖然需要的時間久了點,但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
對于杜仲膠硫化個生産的各項技術,還需要人們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地探索。這就要交給在生産線一線工作的匠人,還有留在實驗室的那幾個小吏了。
就是想到了這一點,謝虞琛當初組建實驗室時,才會專門在一群小吏中挑選出這幾人來。除了作為助手輔助自己完成各項試驗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要培養出幾個懂技術的知識性人才。
這些人不同于現有的木匠或者鐵匠,憑借的是實踐和經驗來獲得某項技術。謝虞琛在培養他們時更注重的是一項項具體的實驗,以及其背後蘊含的原理。
通俗點說,就是不僅知道“要這麽做”,更懂得“為什麽要這麽做”。這些人的技術不是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而是在實驗中獲得的,不僅懂得技術,更明白關于技術的各項理論知識。
這也是他們區別于那些工匠的特點,所以他們具備創新的能力,有改進現有技術的可能。就像在在教授工匠們硫化杜仲膠的方法時,其中一個人就發現了一項新的“二次硫化”的技術。
他發現,在杜仲膠硫化到一定的程度後,即使把加熱的器皿從火上端走。在餘熱的作用下,器皿中的杜仲膠仍然可以繼續完成硫化作用。
這樣做不僅可以去除掉杜仲膠中硫的味道,而且還可以改善杜仲膠的回彈和各項性質,使生産出來的産品更加完善。在驗證了将這項技術的可行性後,他就将其告知了謝虞琛。
在最開始的時候,謝虞琛就在他們之中制定了一個獎懲機制,如果像此人一樣發現了新的技術或者改良了原有的技術,都可以獲得一筆不菲的獎金。
将對方該得的獎金用紅布包了送到他家中後,謝虞琛又開始琢磨起了新的事情。在書房坐了一會兒後,他便起身到了烏菏的房間。
這幾天林場生産的第一批杜仲膠已經被制成了不同尺碼的鞋底。原本謝虞琛計劃着直接将鞋底作為産品銷售。被熟悉經營的管事勸說後才改了主意,決定先加工成完整的鞋子。
不僅省去了向人推廣和介紹杜仲膠優勢的步驟,也有利于在短時間內打開市場。林場當然沒有制鞋的技術,不過這也不是什麽麻煩事。
謝虞琛直接發動“鈔能力”,從其它地方花錢挖來幾個技藝娴熟的繡娘和成衣作坊的員工,又以林場的名義與城中的一間布坊簽訂了協議。在東山州現組出了一個制鞋的鋪子。
除了膠底鞋,制作馬車輪胎和其它東西也在謝虞琛的計劃中的。只不過相比起鞋底,這些産品對于技術的要求就比較高了,一時半會很難穩定生産。
謝虞琛便打算先把其他産品往後放放,優先生産鞋底這一件東西。等到膠底鞋打開市場之後,再着手考慮其它的産品。而烏菏的離開東山州的時間,也定在了杜仲膠能站穩腳跟之後。
……
謝虞琛一進門,烏菏就看出他有話要說,于是直接讓屋裏的侍從都退下。起身給謝虞琛倒了杯熱茶後,才慢悠悠地等着他開口。
“我前兩天和你提過一個人,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謝虞琛徑直開口道:“就是那個發明出二次硫化,改良了硫化技術的小吏。”
烏菏對杜仲膠的生産并不怎麽在意,他此番來東山州也并不是為了什麽杜仲膠。因此對于林場的事,烏菏就只是略知一二。手底下的人想要彙報林場的進展,也被他一揮手給攆開了。
也只有謝虞琛主動跟他說起什麽的時候,烏菏才會對杜仲林場稍微上點心。他對于林場的了解,基本都來源于謝虞琛的口中。
烏菏在記憶中回想了一下,印象裏好像确實有這麽一個人。他點了點頭,語氣不變:“有印象。”
“嗯……就是這個人。”謝虞琛組織着語言緩緩開口,“之前我與那群小吏有個關于獎賞的約定,比如發明新技術、或者發現什麽新的現象、以及改良現有的技術,都會有相應的獎勵。”
“比如這次杜三郎發明了二次硫化,按照約定,應該是賞五貫銅錢的……”
烏菏開口:“但你覺得現在的獎賞還不夠?”
“嗯。”謝虞琛點點頭,對于烏菏能這麽快明白自己的想法有些驚訝。不僅如此許多人都覺得從謝虞琛這兒得錢太容易,什麽改進技術,有新發現,甚至連工作認真,都能得到一些額外的獎賞。
工匠們自然喜歡有一個這樣的上司,但和他同一層面的人,态度便大多相反。就在前幾天,關泰初還借過問林場的收支,旁敲側擊地提醒謝虞琛,意思不外乎他給工匠們的錢有點多了。不過被謝虞琛假裝聽不懂他話裏的言外之意給糊弄過去了。
關泰初覺得為此和謝虞琛失了和氣不值得,便沒再繼續提這件事。不過關泰初這種還不算什麽,在背地裏嘲諷謝虞琛愚蠢的也不在少數。光謝虞琛知道的就有東山州的幾個世家子弟。
烏菏沒有問謝虞琛是不是太過心慈、給的獎賞是不是太多雲雲,而是直接問道:“那你覺得還應該獎賞些什麽?”
謝虞琛想了想道:“這些人原本都是州府衙門的小吏,我想着從職位上,能不能給他們升一下。”
區別于錄事、參軍這樣哪怕是官職極低,但也是有品級的官員,他們這些人雖說是在官府工作,但處理的都是些日常的瑣事,沒什麽真正的實權,也沒有正式的職位。在官衙裏,大概就相當于後世“合同工”和“編制工”的區別。
不過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還是讀過書,肚子裏有點知識學問的。謝虞琛想從官職入手,除了金錢外,他更想要的是讓技術性的人才也能在官府中占據一定的比例。
輕視科學技術也許在現在還看不出什麽危害來,但謝虞琛作為一個現代人,是很清楚後來中國的科技是為何逐漸落後的。
我們先進的技術往往來源于農民或者是工匠的經驗性的嘗試和不同地區的技術交流,極少數才來源于知識分子。但因為我們有足夠多的人口,無數勞動者的智慧凝結起來,才有了技術的領先。
但等到科技愈加發展,經驗性嘗試的弊病就會愈發凸顯,原本需要大量的工匠經過數代經驗的積累才能得到的技術,在具有相關知識的科學工作者的手中,可能只需要幾次在實驗室的嘗試便能得到結果。
就拿杜仲膠的提取來說,如果按照傳統的路子,應該是他們知道如何提煉膠絲後便開始了杜仲膠的生産、在長期的實際操作中,通過不斷地摸索和經驗總結,才能一步步地逐漸提高提煉效率。絕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經過實驗室中的數場實驗,經過不到一周的時間,就能總結出一個高效的提煉方法來。
這就是實驗和推理相較于經驗和直覺的優勢所在。謝虞琛腦子裏的新技術有限,況且以一己之力也不可能讓整個時代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
但他可以盡可能地創造一片适合科技發展的土壤。謝虞琛相信,只要給諸如周喬、杜三郎這樣的人一個适合他們發展的環境,他們能做到的遠遠不止現在看到的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