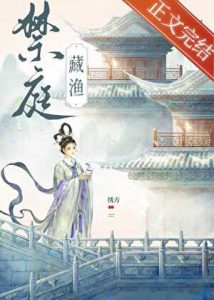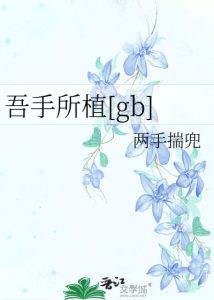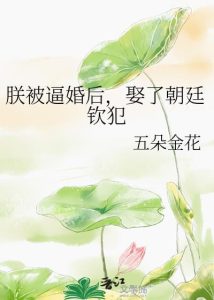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99 章
人力車正式在市面上出現, 已經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時候。
之所以會耽擱這麽久,倒不是人力車的制作工藝又多複雜。之前謝虞琛就說過,人力車的構造極其簡單, 制作起來甚至比現在許多達官貴人乘坐的馬車還要容易得多。
之所以沒有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産和生活中, 主要還是那兩個問題, 木頭車輪和軸承的制約。
現在木頭車輪有了更加輕便減震的杜仲膠車輪代替,而木軸承的替代品——滾珠軸承, 卻不是那麽容易搞定的。
謝虞琛把圖紙送到木工坊的大後天, 徐木匠就将一輛簡易版的人力車拉送到了他面前。謝虞琛讓人拉着車在院子裏跑了一圈,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
沒有滾動軸承的人力車是萬萬不能行的。
作為整個人力車最重要的零部件,滾動軸承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結實堅固。在外力的作用下,不能輕易變形。如此一來,在制作原料的選擇上, 就非常局限了。
在這個年代, 恐怕也只有鋼鐵可供選擇。
對于現有水平的金屬冶煉技術, 和冶煉出來的鋼鐵的硬度, 謝虞琛雖然有點擔心,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在鋼鐵冶煉上, 謝虞琛倒沒有自信滿滿地去摻和。鋼鐵同食鹽一樣,在這個年代都是比較敏感的話題,尋常人誰敢輕易窺探。稍微好奇些,都會觸碰到統治者繃緊的神經。
但謝虞琛不去摻和的原因卻并不是因為這個,主要還是他對于鋼鐵冶煉, 實在是一竅不通。
他穿越來之後所展現的大部分先于這個時代的知識和能力,要麽是平常生活的積累, 要麽是書中偶然習得。當然還有一小部分得益于他演員的身份。
現在影視産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許多打着職業劇的旗號, 實際上整個劇組連一個專業顧問都沒有。
以謝虞琛現在的身份和咖位,接觸到這種草臺班子的概率當然比較小。但即使有相應的專業顧問,謝虞琛還是會自己找一些相對應的書籍資料去學習。
除了不在相關常識上犯錯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麽做能讓謝虞琛盡可能地去融入角色。
但再品類繁多五花八門的職業劇,也不能去講一個鐵匠的輝煌史。謝虞琛能接觸到和冶鐵相關的知識,也只有在高中時,歷史課本上提到的“中國古代金屬冶煉技術的發展史”了。
高中時期起碼和謝虞琛隔了有七八年的時間,即使是記性再好的人,腦海中對于這段知識的記憶恐怕也只剩幾個專業名詞。
對于提高鋼鐵的品質的技術,謝虞琛冥思苦想,也只想到一個百煉鋼,一個灌鋼法。後者是前者的提升。
百煉鋼都得是西漢初年就出現的東西了。顧名思義,通過仿佛加熱鍛打,去除鋼裏的雜物。而灌鋼法雖然也是為了去除雜質,但卻省去了千錘百煉的辛苦和繁複的工作。
謝虞琛記不太清灌鋼法具體出現的時間,具體怎麽操作也只記得是将生鐵和熟鐵中的其中一個澆鑄到另一個上面。
等他找來一個鑄造坊工作的鐵匠一打聽,才知道人家作坊裏這項技術已經用得十分熟練了。
甚至還有生鐵嵌入、生鐵覆蓋、生鐵澆淋等不同的方法,可以根據所造器物的不同選擇。
比謝虞琛知道的那一點皮毛不知道高深了多少倍。
他這個外行只好相信這個年代的冶煉技術,盡可能詳細地畫了一張圖紙,交給關泰初,讓鐵匠試着按照圖紙去鑄造。
外圈和內圈制作起來倒是并不難,只是要稍微費些辛苦。兩個鋼圈的尺寸比較小,相比起工匠們平常鑄造的大物件,需要更加精細。
真正有難度的是裏面鑲嵌的數顆鋼珠。
工匠們嘗試了幾個晝夜,勉勉強強能制造出幾顆來。雖然看起來貌似是個球體,但只要把它嵌到內外圈之間,嘗試着轉動幾下,各種缺陷就暴露得一覽無遺。
因為球體不夠标準,軸承轉動不流暢就算了。努力打磨打磨說不定還有救。
真正要命的是工匠們做出來的鋼珠大小完全不能保持一致。送過來的十幾顆鋼珠裏,甚至湊不出一對大小一致的滾珠來。
謝虞琛看着盒子中的這些“歪瓜裂棗”,深深嘆口氣,無奈地開口,讓一旁戰戰兢兢的鐵匠回去做自己的事情。
怪不得這些個鐵匠們,謝虞琛知道他們已經盡力了,無奈現在的鑄造水平就擺在這兒。
要是什麽鐵器工具的,衆人還能努力一把,直徑一二公分大小的鋼珠,實在不是現有技術水平能造出來的東西。
謝虞琛愁也沒辦法,只好跑去林場的實驗室,靠指點一下裏面的實驗人員來轉移注意力。
後世的實驗室器具大多是玻璃器皿,透明度高,能清晰地看到裏面的物質,而且化學性質穩定,利于清洗。
這年代想要做玻璃可沒那麽容易。而且我們從前的玻璃多是鉛鋇玻璃,和後世的鈉鈣玻璃有着本質上的區別,燒制出來的玻璃大多泛着漂亮的金屬色澤,所以顏色沒那麽透明。
制作玻璃的難度比較大,謝虞琛只好用陶瓷器來代替玻璃作為實驗室的容器,仿照後世的各種燒杯、量筒,畫了圖紙,拿到瓷窯讓人燒了一批瓷質的器皿出來。
燒制出來的瓷器除了不透明以外,其餘方面并沒有多遜色于玻璃。釉面光亮,便于清洗,而且也耐高溫。化學性質穩定,有很好抗腐蝕性,也不會生鏽老化。可以說是一種很好的替代品了。
只是在一旁看着有些無聊,謝虞琛在實驗臺旁邊站了一會兒後就有些待不住了,主動讓其他人給他分配點工作。
稱量溶液或是是其它什麽的,總之不要讓他閑着就可以。
幾個小吏最開始還連連推辭,可能是有點不敢使喚謝虞琛,但耐不住謝虞琛三番五次地要求。
“要不請謝郎幫我清洗一下這些器皿呢?”大家夥兒都覺得清洗器皿是件浪費時間的事,一般不到了最後一個器皿都用完的時候,是沒有人願意做這項營生的。
其中一人試探着指了指一旁在池子裏堆疊着的七八個用過的瓷質器皿。
“可以啊,交給我吧。”謝虞琛點了點頭,走到水池旁邊拿起一副手套戴上。
手套上面塗了一層杜仲膠液,靈便程度自然不能和後世的手套相比,厚厚的一層讓戴着手套的人動作顯得有些笨拙,但為了安全起見,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謝虞琛從水池裏拎出一個小碗形狀的器皿,一般人們會把需要幹燥濃縮的溶液倒在裏面,然後拿去火上烤幹。所以這個小碗比普通的器皿要厚實得多。
不知道上一個用它的人拿這個坩埚一樣的東西裝了什麽,表面摸起來有些滑滑的。
謝虞琛手上戴着厚而笨重的手套,一個沒拿穩,小碗從他手上滑了出去,磕在水池底上,慢慢悠悠地滾了三圈。
“謝郎你沒事吧?”其中一人急慌慌地放下手中的活,轉身朝水池的方向探過頭去。
“我沒事。”謝虞琛頓了頓,撿起滑落的小碗,翻來覆去檢查了幾遍,又補充了一句:“器皿也沒事。”
“……”
“沒事就好。”
剛才拜托謝虞琛去清洗器皿的那個年輕男人,一改往日不愛洗器皿的性子,猶豫道:“不行的話,謝郎還是放着讓我來洗吧。”
“一時手滑而已,放心吧。”謝虞琛辯白了一句,不知道想起什麽,又突然把手中的小碗放到一旁。
緊接着拿起一件瓷器,在水池邊磨刀一樣來回蹭了幾下,又拿起兩個瓷器互相磕碰。
撞邪似的反複了好幾回同樣的動作,連一旁做實驗的幾個小吏都被謝虞琛這邊的響動給吸引了過去,目不轉睛地盯着他手裏的動作,臉上露出一種混雜着無措的震撼表情。
“……謝郎,您這是、在做什麽啊?”周喬鼓起勇氣問道。
謝虞琛扭頭看了他一眼,開口,問了他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你知道陶瓷的硬度是多少嗎?”
周喬來回看了看周圍同樣和他一臉疑惑的衆人,茫然地搖了搖頭。
謝虞琛放下手中的器皿,把手套摘掉後放在旁邊,有些輕松暢意地笑了幾聲後,擡手一拍周喬的肩膀,“告訴庫房,今天在場的所有人,每人賞一百文錢。”
“……”
“啊?!”
誰能告訴他們,怎麽就突然要賞給他們錢了?
衆人面面相觑。有錢拿當然是好事,但也要告訴他們是為什麽賞給他們呀?總不能是謝郎突然心情好賞他們的吧?
謝虞琛現在的心情确實很好,沒有理會衆人複雜的情緒,轉身就要往實驗室門外走。
人們只來得及伸長脖子,沖着謝虞琛的背影扯着嗓子喊了一句:“那這些器皿謝郎還要洗嗎?”
“不洗啦!”謝虞琛頭也沒回,胳膊半擡在空中晃了兩下,做了個揮手的動作,然後笑了幾聲回道:“你們自己慢慢洗吧。”
“……是。”
回了書房,謝虞琛招手叫來了小厮,吩咐道:“你去城東替我把之前給咱們實驗室燒制器皿的那個瓷匠叫過來。”
小厮應了一聲,一盞茶的功夫沒過,便又回了書房,身後跟着一老一少,面露風霜的兩個瓷匠。
這兩人雖然是親生父子,但看起來卻像是爺孫倆一樣。老瓷匠上實際的年齡其實并沒有看上去這麽老。
只是他平日裏又是揉泥又是拉胚。燒窯的溫度動辄上千,即使是開窯的時候,溫度最低也要将近一百度。各種辛苦讓他生生老了十七八歲還多。
“謝郎,您找我?”兩人中年長的父親率先站出來,有些局促地問道。
謝虞琛身邊的仆役來找他的時候,正巧碰上裝窯完畢,他和他兄長準備添柴點火的時候。
這一過程窯膛的溫度要時時刻刻看着,寸步不能離人。但小厮話又說得很急。兄弟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一個留下來看着瓷窯,另一個帶着大兒子過去。這樣瓷窯也不會沒人看管。
謝虞琛點了點頭,打量了一下他身後的年輕人,老瓷匠見狀,伸手把人往自己身前推了推,主動解釋道:
“這是小人的大兒子,小人的兄長在家中看窯,走不開,就派小人和犬子過來……”
瓷匠面上陪着笑,仿佛生怕面前的人會怪罪他一樣,謝虞琛擺了擺手,語氣和善:“沒事,誰來都是一樣的。”
老瓷匠喏喏地應了一聲,謝虞琛又道:“我這次尋你來,主要是有事想問問你。”
“您盡管問,小人一定知無不言。”
謝虞琛笑着點了點頭,打開桌上一個紅木小盒子,從裏面挑出幾顆面相最好看的鐵珠遞到瓷匠面前。
“你看看這幾顆珠子,如果用瓷土團一些和它差不多大小的泥丸,能燒出來嗎?”
瓷匠小心翼翼地接過謝虞琛手中的鐵珠,仔細打量了片刻後才思索道:“小人還從未做過這種圓珠子呢……”
“看着這尺寸是小了點,可能有點麻煩,溫度也不一定對。”
“……不過難度應該不大,讓小人多試幾回,估計能做出來。”
“當真?”謝虞琛為以防萬一,又确認了一遍,但心裏已經基本相信了瓷匠說的話。
用瓷土來制作滾珠軸承裏的珠子,起碼在尺寸上就比用鐵鑄造要簡單得多。哪怕搓出來的泥胚大小不一致,還能揉一揉重新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