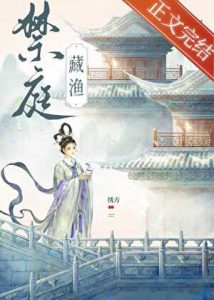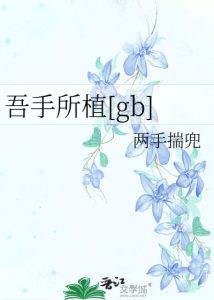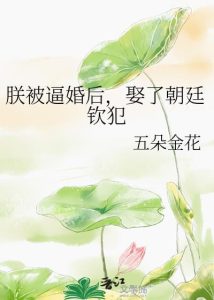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107 章
對于烏菏派周洲來東山州這件事, 謝虞琛自己也表現出了意料之外的驚訝。
這段時間他和烏菏并不是全然沒有交流,信件來往的頻率在後世看來可能不算什麽,但在這個年代絕對算得上是頻繁了。
不過兩人的信件雖然頻繁, 但大多都是在讨論和杜仲膠廠相關的話題。
謝虞琛在最開始就說過不想讓杜仲膠的生産被當地的豪強世家把控, 因此在工匠和人手的安排上就要格外謹慎。
原本謝虞琛只是隐隐有一些尚未成型的想法, 在與烏菏隔幾日一封的信箋中的讨論過程中,才慢慢清晰起來。
最終他決定仿照在東山州建實驗室和木匠坊時那樣, 專門設立一個類似書院的地方用來教授提煉杜仲膠的各項技術。學生自然也不能全從杜仲樹的産地出, 肯定要有一部分從京城或者其他地方選拔。
這樣一來,就能保證在将來建成的林場中,起碼有一半的人手是不由地方管控限制,而是直接隸屬于書院,或者由給予他們權力的朝廷所管轄。
最重要的是, 這些人還是直接掌握最核心技術的人才。
如果是其他人, 說不定會借此機會拉攏這部分人, 将這些人都歸為自己名下, 好借此擴大自己的權勢。但謝虞琛就沒有這方面的想法。
不僅是因為對權勢不感興趣,還有最關鍵的一點就是, 他是個很怕麻煩的人。
因此對于這個目前還是只為了教授提煉杜仲膠技術而開設的書院,在謝虞琛計劃中,最好還是由朝廷直接管轄。這也是為什麽謝虞琛會在計劃開始前就和烏菏頻頻又書信來往的原因。
至于這群人由朝中的哪方權力所屬,比起對他來說兩眼一抹黑的素昧平生的陌生人,還是烏菏更讓謝虞琛信任一點。
哪怕不從理智的角度看, 單從情感出發,謝虞琛肯定也是跟偏向與烏菏這邊。
但對于謝虞琛來說, 不管是玩弄權術還是其它什麽,他都提不起半點興趣。
不然以他的能力和在東山州做的一系列事情, 放在哪個官員身上都是很顯眼的政績。不管在哪個地方,只要謝虞琛想,謀個一官半職都不成問題。
或許取得功名、光耀門楣對于這個時代的大部分人來說,都算得上是畢生理想。但在謝虞琛眼中,這些對他沒有半點吸引力。
甚至不如這個陌生世界的山水草木,某個地方的風土人情來得更讓他感興趣。
不過這件事他謝虞琛沒有跟任何人提過,在這個時代,他好像也沒有熟悉到可以聊這些話題的人。
哦,不對,還是有一個的。
之前他在榆林的時候,烏菏就在信中不太直白地問過這個問題。
如果謝虞琛想要入朝為官的話,能搭上烏菏這條線無疑是最幸運的。
但可惜的是,謝虞琛對做官沒有半點興趣。在其他人看來的漂泊無定,對于謝虞琛來說可從來都不算是奔波勞苦。
他一直就自由慣了,哪怕是從前不進組拍戲的時候,謝虞琛也很少在一個地方長時間地待着。
如果現在非要把他拘在某個地方,別說是入朝做官,哪怕是封侯拜相重權在握,對謝虞琛來說也是一種令他感到煩悶的束縛。
因此在烏菏隐晦透露出這方面的想法後,謝虞琛當即便表明了自己的志向絕不在此,絲毫沒有半點“能在朝中搭上烏菏的關系是令多少人眼紅心熱”的覺悟。
烏菏見謝虞琛語氣決絕,沒有半點禮節性推辭,然後“盛情難卻、卻之不恭”的意思,便也沒再提起這個話題,只當是随口的一句閑聊罷了。
在謝虞琛的計劃中,等他結束了書院這邊的事情,或者杜仲膠廠的生産步入正軌之後,他應當會選擇南下或者是西行。
之前和他有過生意往來的一位姓嚴的年輕郎君跟他提過一嘴,自己從前在南方做生意時的所見所聞,曾途徑的哪些地方雲雲,勾起了謝虞琛的興趣。
那位嚴姓郎君确實是去過不少地方的。據他所說,西行出關之後,風土地貌就完全與南诏不同,不管是當地的環境還是氣候,甚至連那邊人們的長相,都與我們的百姓有很大的不同。
根據這位嚴姓郎君的描述,謝虞琛還暫時并不能确定他說的到底是後世哪個國家或者是民族的人。
而且他所處的朝代嚴格意義上也并不在自己所熟知的歷史中。周邊的番邦外國是不是他記憶裏的那些也未可知。
但這無疑引起了謝虞琛極大的興趣。不止是去親眼瞧瞧,說不定有什麽意外收獲也未可知呢。
現在要緊的就是盡快将書院和杜仲膠廠的事情安頓好。早一天搞定,謝虞琛就能早一天啓程。
在與烏菏的信件往來中,大致的章程謝虞琛已經基本和對方探讨出了一個雛形,只等實際操作的時候去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就行。
不過在烏菏的信中,可從來沒有提過派金甲軍随行護衛的一事,仿佛整件事情是他心血來潮的随性所為一樣。
相比起來的時候,謝虞琛離開東山州時的排場可大多了。
不僅有關泰初等當地官員鄭重其事的餞別宴。馬車啓程的時候,半個東山州的百姓都到了街邊或是城郊送別謝虞琛。
那場面,哪怕是再見慣了離別,再冷心冷肺的人都會不禁為之動容。
謝虞琛把馬車兩邊的車簾撩開,手臂抵着下巴趴在窗棱上。一直到出城送行的人在他的視線中化成螞蟻一般大小,再也看不見蹤影後,他才緩緩直起身子靠回軟榻上,把車簾重新放了下去。
太陽将出未出,天光乍明。掀開車簾後,外面的寒氣似是如有實質地從外面鑽進了馬車,讓人能清晰地感受到天氣已然轉涼。
不過沒人勸說謝虞琛放下車簾。
在謝虞琛身邊候着的人依舊是周洲,他沉默地揣起袖子出了馬車,低聲吩咐了一句,應當是讓人去取手爐過來。
因為在片刻後有一陣馬蹄聲在馬車旁響起,緊接着周洲便從馬車外捧了一個手爐回來。手爐外面還套了一層毛絨錦緞的布套防燙,刺繡精良,一看做工便知價值不菲。
在之前相處的那些時日中,謝虞琛和周洲早已經熟絡了不少。見周洲進來,謝虞琛自然而然地接過他手裏的東西,随口問了一句行程安排。
原本謝虞琛也是做好了出行準備的,行程自然也有規劃。只不過現在有了金甲軍随行,謝虞琛也樂得少操心,直接讓對方接手了這方面的各項事務。
從周洲口中吐出幾個陌生地名,謝虞琛沉默片刻,果斷地停下了接着問下去的打算,“算了,到地方你叫我就行。”
周洲“哦”了一聲。這回在離開東山州的人群中,多了幾個陌生的面孔。看起來年歲都不大,不過一眼能看出來都是幹過活的。
雙手粗糙生繭,但不是周洲這種常年習武留下的繭。關節略微粗大,但是手指非常靈活,腰背佝偻,基本一眼就能判斷出是幹什麽的。
但與周洲所熟悉的工匠不同,那些人身上攜帶者的某種特質,卻是一般工匠所沒有的。
周洲很難用語言去形容那種與尋常工匠的不同,他心想,畢竟是謝郎身邊的人呢,特別一點不才是最正常的嗎?
不過當他們遇上一身甲胄的金甲軍士兵時,面上難以掩飾的畏懼還是很明顯的。
在吃飯的時候,周洲有心想跟這些個木匠套個近乎,好弄明白謝郎為什麽會對他們另眼相待。
只不過還沒等他靠近,那些個木匠就端着自己的飯碗,警惕而小心翼翼地後退了一步。搞得周洲一臉懵逼地站在原地,不知道下一步是該退還是該進。
最後還是謝虞琛笑着叫住他,讓他別去吓唬人家。
周洲:“?”
他怎麽就是吓唬人家了?他明明只是想和對方交好的。
不過除了這些新面孔之外,謝郎身邊經常跟着的那個名叫餘小郎的半大男郎卻不見了蹤影。周洲有些疑惑地問了管事一句:“謝郎身邊的那個小郎君呢?”
“大人說的是餘小郎吧?”管事笑着說道。
見周洲點頭,管事這才不緊不慢地解釋:“原本謝郎也是打算帶餘小郎一起去梁州的……”
“那我怎麽沒看到他?”周洲問。
管事笑道:“但謝郎這一走恐怕不是又要忙活到明年嘛。謝郎就想着餘小郎也有一年多沒回過家了,之前在榆林的時候,家裏隔段時間還能讓人捎封信過來。”
“但自從來了東山州,山高水遠的,寄信也不方便,就算是小郎自己不想家,家裏人估摸也想得緊了,就想着要不讓小郎回一趟家,等到明年開春,再随商隊一同來梁州這邊也行。”
“前些日子謝郎給他阿姊姊夫寄了封信,他阿姊姊夫也是這個意思。正巧遇上從江安府來的商隊,謝郎與他們管事也相熟,便托對方将餘小郎帶到江安府,跟他家裏團聚些時日。”
周洲回憶了一下自己去年見到那小郎君的時候,雖然言行談吐就跟個小大人似的,行事比京城許多世家家中的小孩還要周全成熟得多。
但只看模樣就知道,那餘小郎的年歲并不大,周洲估摸頂多就是十來歲。
這麽小的孩子,若是放在他熟悉的那些人家,家裏人都不知道怎麽寵着呢,生怕磕了碰了,或者在哪受了委屈。哪怕是周洲自己,在和餘小郎一般大的時候,都還在爺娘身邊耍賴撒嬌地不肯念書習武。
餘小郎這麽小的年歲就跟在謝郎身邊,闖蕩也好,見世面也罷,都不是一般小孩能吃得了的苦。
收獲的機遇和閱歷……自然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而且還是謝郎手把手教出來的學生……
周洲默默地感嘆了一句,這小郎君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啊!
不過現在的餘小郎還沒有生出這方面的心思,他坐在商隊的拉貨的馬車上,左手拿着烤餅,右手握了水囊,狼吞虎咽地吃飯。
謝虞琛既然會把他托付給這隊商隊,肯定是确信對方在待遇上不會苛待餘小郎。
當然事實也确實如此,商隊的管事待餘小郎确實算得上一句“周到”。哪怕是走夜路趕行程,管事都不忘給餘小郎添床被褥,關照他晚上睡覺冷不冷。
前些時日餘小郎主動想辦商隊做些零碎的活計,也都讓管事故意板着一張臉給拒絕了。
只不過他們到底是急着做買賣的商隊,在行程上不可能跟以游歷為目的的人們相比,那般自在悠閑,多少還是要辛苦一些的。
餘小郎雖然跟在謝郎身邊時,處處有人照看,但他自己是很能吃苦的,因此倒也不覺得跟着商隊趕路是一件多辛苦的事情。
讓他感到茫然無措的,更多的還是心裏翻騰的各種情緒作祟。紛繁雜亂,理不出個頭緒來。
現在餘小郎的心裏,一邊是對于阿姊和故鄉的思念之情不斷拉扯着自己的心髒,讓他恨不得插上翅膀立馬飛回蓬柳村。
但另一邊,歸心似箭的急切又被另一種情緒堵着。
這種情緒要更深刻,也更複雜。讓餘小郎在感到期待的同時,又有些沒來由的恐慌。
馬車在夜色中辘辘行駛的時候,不知道為何,餘小郎突然想起了他離開蓬柳村時,謝郎問過他的一句話。
謝郎問他:“将來想做什麽?”
餘小郎閉上眼睛還能分毫不差地想起當時的情景——
謝郎詢問他時的神态,他當時是如何回答,心髒又是如何激烈地跳動。
但如果讓現在的他再次重新回答這個問題,他真的還能再那麽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要所有人都吃飽飯”嗎?
讓若有人都吃飽飯……
他當時是懷着怎樣的心情将這句話說出口的呢?
這真的是自己真的能做到一件事嗎?
在跟着謝郎見識過那麽多人,經歷過那麽多事後,他還有信心和勇氣說出同樣的回答嗎?
餘小郎忍不住問自己。
這不是,也不可能是你一個人能做到的事。
這需要無數像他一樣的人,也許窮極一生的努力也無法到達那個目的,但只要一步步往前走,他們就會離那個目标一步步更近。
“不是嗎?”謝虞琛把他随手撿來的一根羽毛制成的蘸水筆扔到了一旁,擡頭瞥了一眼周洲,“難道這兩個數相乘的得數不是三千六百一十二?”
周洲伸長脖子努力看着紙上的算式,不知過了多久才像剛回過來神似的,點了點頭,心虛一笑:“好像是算錯了。”
“不是算錯,是又算錯了。”
謝虞琛無奈,這已經是周洲算錯的第不知道多少道題了。可能計算他哪道題做對了,還要更簡單一點。
前兩天謝虞琛覺得百天內趕路無聊,正巧周洲問起他當初在寶津渡時教茶樓衆人的算術法,謝虞琛便只當是打發時間不過,教了衆人幾句豎式計算,還有一些簡單的體積公式。
豎式計算并不是什麽複雜東西,跟在謝虞琛身邊的人基本都會。
最開始他們也不覺得這豎式計算有什麽精妙之處,直到後來在生活裏用上了這個法子,衆人才意識到這計算方法到底有多方便。
之前遇上什麽需要算計的數字,肯定得去搬算盤出來,但那算盤珠子又不是人們天生就會撥的。而且也不是每次都有時間讓他們拿出算盤放在桌子上慢慢撥算。
但謝郎教的這些方法可不一樣,別說是桌子了,哪怕你沒紙沒筆,從樹上折根樹枝,蹲在地上就能直接計算,不知道有方便了。
一傳十十傳百,所以現在基本從謝虞琛身邊随便拉一個人出來,都能熟練掌握這種計算方法。
但周洲是個例外,謝虞琛也是直到教了周洲兩天,發現他還是算不對自己出的算術題之後,才發現這人在算數上是一點天分都沒有,甚至到了一種離奇的地步。
就比如剛才,就是最簡單的一道兩位數乘三位數的乘法,放在小學三年級以上,不用二十秒就能算出答案的算數,周洲連着算了三遍,都沒算出正确的結果。
而且這三次算出來的答案還都各不相同。
謝虞琛也是第一次見到周洲這種人,在無語和震驚的同時竟然還生出一點“我一定要教會他”的執拗。
但在親眼看着周洲連錯七道題之後,這種執念也化作一縷青煙,伴随着謝虞琛深深的嘆息而煙消雲散了。
周洲你是真的牛啊!
謝虞琛忍不住開口:“周洲你平常出門買東西的時候,……掌櫃會多算你錢嗎?”
周洲搖頭:“我沒注意過,不過我跟在大人身邊,吃穿用度什麽的……”周洲很實誠地回答,“也少有需要自己買點什麽東西的時候。”
“挺好的,省的被坑。”謝虞琛深吸了一口氣。
……
謝虞琛人還在路上,但關于第一批杜仲膠廠人才的選拔已經開始了。
人們也是第一次聽說還有這樣的“書院”,既不教人詩文經義,也不教人騎射之術,反而是要教人們學習什麽杜仲膠的生産。從書院出來的人也不去衙門做官,而是去那什麽杜仲膠廠。
說來也是奇事一樁。
“這不就是跟去作坊做工差不多嗎?什麽時候去作坊做工還得學習了?”臨街的茶攤中,傳來一個男人不屑地嗤笑聲。
“你說什麽呢?看沒看過告示啊。”
男人話音剛落,人群中立馬有人反駁道:“告示上說的清清楚楚,在書院學習通過考核之後,書院會安排到各地的杜仲膠廠做管事。”
“管事又如何?”那人面子上過不去,硬着頭皮繼續犟道:“真是一群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一個破作坊的管事……有什麽稀罕的。”
這話大家就很不愛聽了,你是個什麽了不得的人物嗎?就嫌棄起管事的地位不夠格了?
衆人雖然心中忿忿,可畢竟拿捏不準說話人是什麽身份,一時間竟被男人的狂妄給唬住,不敢繼續反駁了。
“破作坊?破管事?”旁座一桌沒有說話的人突然冷笑一聲,“我倒是不知道,這京城中的人眼光竟是如此之高了嗎?”
他說着一站起身,在衆人的注視中走到剛才口出狂言的男人面前,語氣不疾不徐:
“我倒想問問你——
你可曾見過東山州連綿千畝,一眼望不到邊際的杜仲林?可曾親眼見過整齊俨然的杜仲膠生産廠房?
又是否見過實驗室整夜明亮的燈火?見過裏面秩序井然,分工明确的工匠?”
——如果這些你都沒有見過,那麽你憑什麽上下嘴皮一碰,就說那是個破作坊。
“最關鍵的是,你知道杜仲膠廠運轉一日,能夠生産多少杜仲膠,它們又價值幾何嗎?”
男人直直地看向對方,“這些你都知道嗎?”
明明是極為平靜的語氣,被他一句一句說出口口,卻莫名帶上了極重的威嚴。
人群中不知道誰叫了聲好,剛剛還在大放厥詞的那人強忍着懼意沒有後退。
但任誰都能看出,他的內心已經慌到了極點,竟是連一句反駁的話都不敢說,從懷裏摸出幾枚銅錢丢到桌上後,便在人們的奚落聲中,頭也不擡地奔着大門沖了出去。
“這位郎君看着面生,聽口音也似乎不像京城人士?”
因為剛才的一幕沸騰起來的氣氛逐漸冷靜下來後,人們才注意到這位面容清秀的年輕郎君。
“某确實不是京城人士。”
“諸位剛才不是在讨論為杜仲膠開設的書院嗎?”男人很好脾氣地笑了笑,似乎剛才冷聲質問的人不是他一樣,“等到書院建成之後,我便是裏面的其中的一個講師了。”
茶攤頓時一片嘩然,他們私底下随便閑聊幾句就罷了,竟然議論到了人家書院講師的頭上,這可真是……
不過對方似乎并不介意他們這番無禮的舉動一樣,伸手将剛才男人落荒而逃時不慎撞倒的長凳扶起來,對衆人緩聲道:
“大家夥對書院感興趣是好事,若是有機會,說不定咱們還能在書院再見呢。”
人群中不乏有對書院感興趣的,聽到這話,也趕緊應和了一句,有幾個膽子大點的這位未來的講師面善,還站出來詢問了一些關于書院的問題。
書院是官府背書,又有白紙黑字的告示貼出來,人們對于這封“招生啓事”的信任度還是比較高的。
只是畢竟從前從未有過先例,對于那些聞所未聞的條例,大家心裏難免有些沒底。
“我聽人說,書院選拔不看名聲那些,所有人都能參加選拔,可是真的?”
這年頭,某某縣的哪個郎君有什麽名聲,聽着似乎是很厲害,也是選拔人才的重要标準之一。但說白了,這些都是虛的東西。
當然也有因為名聲得到上面注意,最後平步青雲的人,但那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大部分人能不能成為“入選的人才”,還是由彼此的家世決定的。
這也是為什麽杜仲膠廠開辦會成為這段時間衆人議論的重點的原因,實在是那句“不論家世,只看學問”,戳到了人們心中最深的那個地方。
“當然是真的了,不是都寫在告示上了嗎?”男人似乎笑了一下,“學院的選拔只看你們各自的真才實學。只要進入了學院,不管家世如何,大家都是站在同一起點的人,學習的內容也是一模一樣的。到時候誰能通過最終的考核……”
他沒有把話說完,但衆人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
全憑各自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