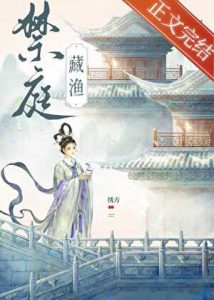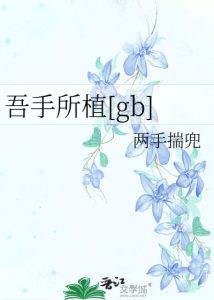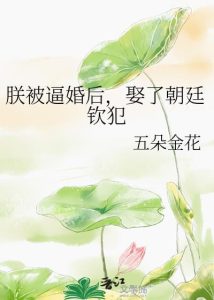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108 章
學院正式開始上課前, 為了鼓舞學生的士氣,先把學生們都集結在前院,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動員大會”。
這個衆人聞所未聞的大會當然是謝虞琛建議書院開辦的。
這和他前世拍戲, 劇組也會在開拍前舉辦開機儀式一樣, 不一定有什麽實際上的作用, 但如果不辦一個的話,總感覺缺了點什麽似的心裏安定不下來。
而且通過書院考核的這些年輕人還和後世學校的學生有一些不同之處。
按照謝虞琛的要求, 書院在選拔時, 只關注學生的才能和天分,并沒有對其家世背景有任何要求。
再加上那些世家子弟們自持身份,也不願與這群布衣百姓混跡在一起。因而書院的第一批學生,基本都是些自身天賦不錯,但是因為家境貧寒沒有出頭機會的人。
雖然不管是招生時的管事, 還是後來在書院裏遇上的先生, 都再三跟他們強調過, 不論家世好壞, 書院對他們都是一視同仁對待,但到底是第一次, 衆人心中難免惴惴。
書院在他們入學前開辦這麽一個“動員大會”,一定程度上也安了不少學生的心。
學院是按照謝虞琛的指示和要求一點一點開辦起來的,但謝虞琛并不負責日常的教學。書院的學生們只是聽過謝虞琛的名字,對于他本人,大多在動員會上才是第一次見到。
謝虞琛并沒有在會上多待, 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書院的辦學宗旨和杜仲膠廠的發展方向之後,便匆匆離去, 消失在了院子的側門外。臺下的許多學生還因此露出了點失望的神色。
書院的院長苗文和是一個面容白淨、氣度儒雅的男子,約莫三十來歲, 舉手投足之間能看出他良好的教養。
書院的先生大部分是跟着謝虞琛從東山州離開的那些人,熟悉杜仲膠的生産技藝,雖然在林場的時候也被謝虞琛安排着念了點書,但氣質和傳統的讀書人還是有很明顯的差距。
少數幾個謝虞琛聘來負責書院基礎的文化知識的先生,倒是端了一副讀書人的架子,但和文質彬彬的院長苗文和站在一起,立馬就能看出二者之間巨大的差異。
不僅是書院的衆人,謝虞琛最開始也有些疑惑,這樣一個一看就家世不凡的人怎麽會來他們書院?
而且以他和書院其他人截然不同的出身,真的能和書院相處融洽嗎?
不過此人是既烏菏安排來的,出于對烏菏的信任謝虞琛并沒有質疑。而這段時間以來苗文和的表現也證明了自己确實值得謝虞琛和烏菏的信任。
不僅如此,謝虞琛還發現了一點——
書院的學生雖然都是聰穎伶俐之人,但到底在這種等級分明的社會中浸染了十幾年,對于苗文和這樣的出身,天然帶有一種敬畏之心。
這就使得苗文和在管理書院時,出于對于他身份的敬畏,學生們會更加聽從他的安排。
謝虞琛從側門出去,離開衆人的視線後,并沒有離開書院,而是繞了一圈又回了書院的另一頭。
這裏原本是為先生們日常辦公和休息而建,為了和學生隔開,還專門在院牆外面栽種了一排樹木。不過現在大家都去了前院參加動員會,這裏自然就空了出來。
雖然謝虞琛不常來書院,但這邊還是給謝虞琛專門留了一間采光不錯的屋子。
屋裏的擺設很簡單,一套桌椅、一排書架、幾個櫃子,還有一張用來休息的矮榻。書桌上放着幾,旁邊是一疊裁好的白紙。
但桌上的書籍裝訂精良,字跡清晰,裁好的紙張亦是光滑細膩。
這年頭的紙價雖然沒有貴到買不起,但也是普通人舍不得消費的東西,這種品質的紙張更是市面上少有。估計只有作為貢品的宣紙能比得上。
紙上是謝虞琛自己出的試題。
既然是要開辦書院,沒有相應的教材怎麽行。在這方面書院從上到下沒一個內行,對于謝虞琛想要的那種教材更是兩眼一抹黑。
好在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謝虞琛雖然沒編過教材,但他可是實實在在上了十幾年學的人,帶着書院的衆人熬了小半個月,照貓畫虎地倒也編出幾本像模像樣的書來。
不過這些書裏的內容都是最基礎的知識。
書院第一批的學生有将近兩百來人,不可能都是讀書搞研究的料子。
有相當部分學生會在書院學習一段時間,學會了杜仲膠制取的相關技術後,就要去各地的杜仲膠廠任職,并不會在書院待太久的時間。
他們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通過一期又一期的考核,留在書院裏,像一塊海綿一樣,汲取這個時代最先進的科學知識。
謝虞琛想着,既然有了合适的教材,那怎麽能缺了試卷呢?沒有經歷過噩夢一樣考試的學生時代是不完整的。
作為一手創辦書院的人,謝虞琛怎麽能讓學生們在書院的生活缺少了這麽重要的部分呢?
不過出試卷也是一個複雜的活計,題目的難度既不能太高,容易打擊學生的自信心,但也不能太容易。
為了這個試卷,謝虞琛好幾天都沒歇着,終于在今天出完了最後一套試題。
卷子出完之後還要印刷。這年頭印刷術還沒有大量流行開來,書籍文化的主要傳播手段還是靠人們手抄。
謝虞琛跟書院衆人提起刻雕版、印刷書籍的時候,除了苗文和不露聲色地點頭之外,其他人都是一副“從來沒聽說過啊”的茫然樣子。
其實雕版的原理并不複雜,印章在這年頭都已經成了文人雅士觀賞把玩的藝術。雕版印刷說白了就是大了幾碼的印章。
雕版印刷技術沒有流行開來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識字的人太少,還有人們對于書籍的需求不大的緣故。
如果印刷的數量太少的話,相比起每翻一頁書就需要刻一塊雕版的方法,顯然還是手抄要更劃算些。
雖然印刷整的成本比較高,但雕版技術用來印刷卷子還是很合适的。
再加上謝虞琛從東山州帶來的那幾個木匠,現在已經成了書院的先生,他們原先的手藝都還在,制作幾塊雕版對他們來說簡直輕而易舉。
等到書院在南诏打出名聲之後,這些卷子還能賣到別處去也說不定。
……
京城作為整個南诏的政治中心,除了淮陵那種格外富庶的地方,基本上整個南诏最鼎盛的世家大族都集聚于此。
這樣的地方素來是不缺乏新鮮東西的,可能放在別的地方要議論上幾個月的事情,在京城不過是茶餘飯後的一頓閑談,之後便會被人忘卻在腦後。
不過最近幾個月,有一個名字倒是一直在衆人關注和議論的中心。
若是在之前,有人被那些素來眼高于頂的世家們注意到,不外乎兩種可能——要麽是此人的出身或是門第不凡,要麽就是做出了什麽刻意博人眼球的舉動。
但這回卻不同于以往,身處在輿論最中心的這個人不僅沒有故意博人眼球炒作,行事風格反而稱得上是低調。
京城中有名有姓的世家郎君們都對此人好奇不已,卻不見對方出席任何一場他們舉辦的宴會。衆人也從未聽說他們中的誰與之交好了的消息。
只要搭上他們這些世家中的任何一個,将來的人生不能說是順風順水,但也是一片光明,但人家他們這些世家卻沒表露出一丁點的在意。
傳聞中唯一能和對方搭上線的,是淮陵第一世家。但就算是沈家,提起和對方的關系時都一副含糊其辭的模樣,仿佛這個關系還是沈家主動攀上去似的。
自然有人懷疑對方如此特立獨行,不過是為了引起他們的注意,博取名聲和關注。但這樣的言論剛出現,就被人嗤之以鼻地怼了回去——
別人想方設法、費盡心機地營銷自己,不外乎是想要名聲大噪,之後說不定能得到上層統治階級的關注,從而有機會出頭。
但若是人家根本不缺出頭做官的機會,又怎稀得博取他們的注意。
如此說來,倒真是個奇怪極了的人。
……
其實早在一兩年以前,這群對謝虞琛好奇得抓耳撓腮的世家郎君就曾在無意中和他打過交道了。
只是一個根本不在意世家的看法,另一個還沒有意識到對方就是如今被整個京城議論和關注的人。
那時候京城剛流行開一種裝在瓶子裏的有香味的液體,販賣這種液體的商販們稱呼其為“香水”。
據說,發明這種香露的人就是這麽稱呼它的。
“香水”這名字倒是直白好懂,哪怕是第一次見到香水的人,聽到這個名字之後都知道那瓷瓶裏裝的是什麽東西,但卻缺少了一點精致的意趣。
明明是一樣芳馨雅致的物件,平白被這個名字染上了幾分俗氣。這在一群愛好風雅的世家郎君眼裏是絕對不能忍的。
因此香水剛到京城不久,便被人冠上了各種各樣的別名。就連售賣香水的鋪子,為了迎合世家郎君娘子們的喜好,也都紛紛花高價請人改了名字。
衆人也是驚訝,光看這香水的包裝,瓷瓶顏色淡雅,式樣也獨特,撇口短頸,器身細長,形似柳葉,怎麽看都不像是會起出“香水”這種大白話的名字的人。
可能能從花朵植物中提煉出香液的人,就是與常人有一些不同吧?
香水在京城快速地流行開來後,那些世家郎君也派人打聽過香水背後之人的身份,有沒有合作的可能雲雲,不出所料都被對方婉言謝絕了。
大家一個個都是人精,那香水作坊所謂的管事一看就是個被頂出來負責日常經營的“面子”,真正的掌櫃估計另有其人,多方打聽無果後便也歇了心思。
說到底,衆人對于這位神秘的香水發明者的好奇心還沒到了要興師動衆結識對方的地步。
大家四下議論了幾日後,便被更新鮮有趣的東西吸引了注意,把已經走水路抵達東山州的謝虞琛給抛在了腦後。
時至今日,在京城,香水這東西早已經不是一個什麽讓人新鮮稀罕的物件,而是作為生活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進入了這些世家兒郎們的日常之中。
先不提那些富貴人家的郎君娘子們每日出門前必定要往衣襟、手腕處塗抹一點香水,香水的種類也愈加豐富。郎君娘子們不僅有偏好喜愛的氣味,甚至還會根據自己當日的服裝和天氣選擇不同的香水品類與其相配。
喜好風雅的年輕人們時不時還會舉行個什麽品香會、調香宴之類的活動。香水除了最本身的用處之外,顯然已經被賦予了另外的屬性,甚至隐隐有了朝着藝術方向發展的趨勢。
在他們在興致勃勃地參加各種品香宴,以及向同伴炫耀自己新調的一款氣味清爽的柑橘調香水時,還尚且不清楚——
他們近日關注的重點,和發明出香水這一物件的神秘人物,竟然奇跡般的重合了身份。
“我說,就算這人确實不似尋常,但你們也不至于每次出來都把這人拎出來談論一遍吧?”
京城最大的酒樓中,一個衣着光鮮的年輕郎君懶洋洋地抱怨道:“你們再這樣,下回我可不同你們出來了。”
“別嘛。”
聞言,沉浸在讨論中的衆人趕緊回過神來,紛紛開口道:“不說了,不說了還不行嗎?”
“不過,我說子義,你難道對這位謝郎就沒有一丁點的好奇?”
“你叔父不是在漢中任職嘛,我記得漢中那一帶也是有杜仲樹的,你們家難道不打算争取一下那杜仲膠廠?”
“對呀,周郎難道沒聽說什麽消息?”
“倒也不是……”見衆人都盯着他,最開始出言抱怨的那人只好嘆了口氣,把自己從家中長輩聽來的消息挑着同衆人分享了幾條。
他不僅有一個在漢中做官的叔父,還有一個做國子監祭酒的父親。
這個身份在京城雖然不算顯赫,但因着整個京城大小書院都歸國子監統管,作為國子監的長官,學識和聲望缺一不可,坐在這個位置上的人,身份地位便也比同品級的其它官員要高貴些。
而這個自開辦伊始就飽受關注的杜仲膠書院,雖然地點離京城稍遠了些,但據說是為了日後做研究方便,實際上還是應該在國子監的管轄範圍之內。
按理來說應該是這樣,但實際操作起來要更複雜一點,各方掰扯到現在也沒一個結果。
第一個原因前面說過了,書院的學生大多家境貧寒,有一部分人甚至是工匠出身。但國子監底下的六學是什麽情況?
能在裏面上學的人全都非富即貴,即使是四門學中,真正家境貧寒的學生也沒有幾個。讓這些人和他們素來瞧不上的人有牽扯,各位世家郎君心中是一萬個不願意。
而且杜仲膠書院的課程內容也和尋常書院不同。
前些日子書院日常教學的內容送到國子監去,幾個主薄圍着研究了半天。上面的每個字他們都認得,但組在一起之後怎麽就那麽晦澀不通呢?
但衆人也不好意思承認自己知識淺薄,畢竟人家送來書冊的時候就說了“這是他們書院一些比較基礎的東西”。
在座的主薄最差也是熟讀經義、通曉五經四書的人,怎麽好意思承認自己連人家基礎的書目都看不懂呢?
連人家教授的課業都搞不清楚,國子監自然也不太好意思對書院的管理指手畫腳。衆人推三阻四,你推給我我推給你的,都不想接這個燙手山芋。
萬一自己哪做的不到位,被人家看出來其實對書院教授的知識一竅不通,那可就丢人丢大發了。
況且他們也被族中長輩叮囑過,這杜仲膠書院看起來好像不起眼,但裏面的水可深了去,各方勢力摻雜,連最不好惹的那位據說都牽扯了進去,這趟渾水他們還是不蹚為好。
前些日子提起此事時,國子監和禮部的人有一個算一個,紛紛站出來表示,書院既是為杜仲膠廠設立的,教學的內容也不同于尋常五經六藝,讓他們來管自然不太合适,還是工部的各位大人能者多勞得好。
工部衆人一聽,這說的叫什麽話?你們不想摻和這趟渾水,難道他們工部的人的頭就格外鐵嗎?也都紛紛推辭——
哎呀各位大人說得這叫什麽話,一直以來教導諸生的職責不都是國子監的各位大人掌管嗎?
雖然新設的書院在課業上與尋常不同,但我們工部的人哪懂什麽辦學治學呀!
還是各位大人學識淵博,想來一個小小的書院怎麽可能難倒各位大人呢?
說起這件事,周郎周子義也是愁得要命,他父親可是國子祭酒,整件事裏最倒黴的一個。
那日下朝回家,他可憐的老父親坐在書房裏嘆了整整三個時辰的氣。中午的時候就連飯桌上最愛吃的紅燒肉都沒動幾口。
想當初就連生病被郎中再三叮囑不可碰油膩之物,都沒攔着他老父背着他到酒樓吃紅燒肉解饞。現在卻連紅燒肉都失去了吸引力,由此可見祭酒大人确實憂愁到了一種地步。
“要我說啊,子義你也不至于這麽擔心,別看那書院現在熱鬧,據說裏面連博士和學正都是木匠擔任的。”同伴撇了撇嘴道:“誰知道能開到什麽時候。”
其他人也點點頭附和道:“那書院的課業确實奇怪,盡是些聽都沒聽過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