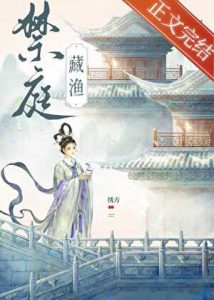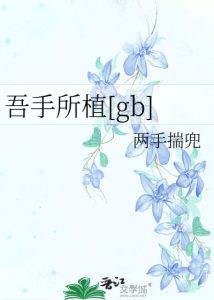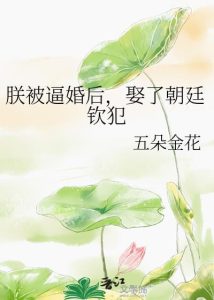幫工
已經休息這樣的話自然是說辭,事實上,謝虞琛正在後院琢磨如何做泡菜呢。
這幾天新院子的修建已經到了收尾的階段,許大郎種下的蔬菜也陸續成熟,謝虞琛便把注意力放到了這些蔬菜上。
前幾天,謝虞琛讓許大郎專門找人定做了不少有檐的壇子。
蓋上內蓋和外蓋之後,再在壇檐四周倒一圈水,就能很好地隔絕空氣和灰塵,防止雜菌進入壇子導致發酵失敗。
按照謝虞琛給的圖紙,燒出來的壇子和後世的那種泡菜壇子相差無幾。許大郎租了一輛驢車拉回來,大大小小地擺了半個院子。
最大的那幾個壇子高度幾乎和許大郎的膝蓋齊平,用來腌酸菜。
小一點的謝虞琛則打算腌些胡瓜也就是黃瓜,還有蘿蔔之類的泡菜。除了地裏中的白菜,謝虞琛還讓許大郎買了十來斤芥菜。
清洗過表層的泥土之後,謝虞琛便讓人把它們懸挂在院子裏蒸發掉水分。等到菜葉表面變得有些發蔫之後,就可以裝壇了。
壇子清洗晾幹,再往裏倒一圈白酒,既能消毒殺菌的作用,還能增加酸菜的風味。
酸菜制作起來并不麻煩,用料也簡單。除了鄉裏人家幾乎家家戶戶地裏都有幾棵的蔬菜以外,只再需一味食鹽做調料即可。
節儉一點的,直接用粗鹽,還能再省下幾文錢。
把鹽粒均勻地灑在葉片上,再塞進缸裏,壓上一塊體型勻稱的大石頭。
石頭是許大郎從河灘上一塊一塊挑揀出來的,頗有些分量。往家裏搬的時候,叫了好幾個漢子幫忙,才運回來。
五六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各個扛着塊青灰石頭往村裏走,那場面怎麽看怎麽怪異。
再加上領頭的那個還是最近村裏風頭最盛、議論最多的許大郎,村人們好些都跑出去看了熱鬧,私底下也議論起來,猜測着河灘上那些不起眼的石塊究竟有什麽用處。
這幾日,蓬柳村有一半的人都眼巴巴盯着許家院子,想着萬一許大郎又整出什麽新鮮物什來,他們也好跟在後面喝口肉湯。
畢竟誰沒看見過跟許大郎賒貨的那些人?他們挑着擔子,走街串巷地賣着許家食肆的各色吃食,一個個的都賺足了銀錢。
只可惜他們腦子轉得比那些人慢了幾個彎兒,等他們嗅到了商機,許家食肆早就已經不應許人賒貨了。
說是人手有限,每日備不出那麽多貨來。
“不能再擴招人手嗎?”許大郎也問過這個問題。
謝虞琛沒有同意。他粗略地計算過,當前附近幾個村縣,對于食肆的需求已經接近飽和,即使他們還能生産出更多的商品,也沒有那麽多的消費者。
但若是要擴大市場,現在的運輸速度又達不到,等到吃食運到了那裏,也都變質不能吃了。
這些都是旁人不知道的。他們生生錯過這麽一個賺錢的機會,只覺得腸子都要悔青了。但也沒辦法,那許大郎跟頭倔驢似的,說不賒就不賒。
許家食肆有十幾個多身強力壯的幫工,還有陳家派來的雜役。
這些人就是想放刁撒潑,也不敢在他們面前耍橫,只好陪着笑,央求許大郎再有什麽賺錢的好生意,一定要先考慮他們這些同村的鄉裏鄉親,莫讓那些外鄉人再搶了先去。
……
壓上石頭後,酸白菜就可以封缸了,但隔壁壇子腌着的芥菜還缺最後一步。
謝虞琛讓許大郎從廚房端來一盆淘米水,“噸噸噸”地倒進了壇子裏。
加淘米水自然是為了加速泡菜發酵的過程。
封蓋後的酸菜被許大郎和另一個在許家做事的年輕郎君合力搬到了南屋避光的角落。
封好的酸菜壇子從外表是看不出區別的,為了分辨這幾壇品類不同的酸菜,謝虞琛還特意找來幾張粗麻紙,在上面寫了“白菜”、“芥菜”幾個大字,沾了漿糊貼在壇肚上。
“公子,這樣酸菜便做好了嗎?”
見他出來,站在院子裏圍觀的衆位庖廚立馬圍上來,你一言我一語地問道。
謝虞琛打了一瓢水,一邊清洗手上剛沾上的一點漿糊,一邊向衆人解釋酸菜制作的原理。
說到發酵時,有人恍然大悟道:“這不就和咱發面蒸籠餅一樣嗎?只是我還從不知道,那芥菜也能像籠餅一樣發酵嘞!”
“原理都是差不多的,只不過酸菜需要發酵的時間要久一點,起碼得一個多月。”
謝虞琛擦幹淨手,又讓他們把剩餘的幾個壇子也一并搬過來,準備做泡蘿蔔和酸黃瓜。
這倆的做法比酸菜要複雜許多,雖然用不了那麽多食鹽,但需要的調料卻比酸菜多了好幾種。
許大郎從廚房裏端出來兩個陶碗,一個裏面裝了姜片、蒜瓣、花椒、糖等七八種調料,另一邊則是滿滿一碗醋。
謝虞琛指揮着許大郎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把醋和熱水混合起來。
他們用的醋質量一般,吃起來會有一股劣質的醋酸味,被熱水一激能揮發掉不少。
另一邊,幾個手腳麻利的幫工也将蘿蔔切成了合适的大小,用鹽殺出了小半盆水。
餘下的步驟和剛剛腌酸菜時差不多,衆人娴熟地将胡瓜和蘿蔔都腌好,一并搬到了屋子裏。
唯一可惜的是這個時代還沒有辣椒,謝虞琛只能用了幾顆茱萸代替。茱萸雖然也能提供辣的味道,但多少會帶着些獨特的苦澀。
謝虞琛不知道用茱萸做出來的酸蘿蔔會不會好吃,以防萬一,就只在其中一壇裏加了茱萸。萬一味道不對,損失的也不多。
院子裏的蘿蔔還剩不少,一次性腌不完,謝虞琛便幹脆讓人切成卷,挂在院子裏繼續晾着。
晾幹後的蘿蔔可以存放很長時間,什麽時候想吃了,就用熱水一泡,再拌點鹽醋一類的調味料,也是一道不錯的下飯小菜。
最近天氣幹爽,修院子的工匠們也打算在這兩天把牆刷了。
這樣的天氣會讓牆體裏水分更快蒸發掉,也不會突然來一場雨把牆面給澆透了。
打灰刷牆這一步驟自然是謝虞琛要求的,用的是石灰和砂石混合而成的石灰砂漿。
蓬柳村氣候偏潮,冬天濕冷。刷一層石灰砂漿除了能讓牆體更加堅固以外,也是為了提升建築的防潮保溫效果。
但石灰石這種東西他們蓬柳村是沒有的。村外的河灘上也撿不來。
謝虞琛最後只好托了陳汀幫忙,從更北的地方運回來。
這一趟光路費就花了不少錢,均下來一車石灰石價格接近百文,實在不是普通人家能消費得起的。
即使是最近生意爆火,謝虞琛也只舍得和上砂石,在牆面上這麽薄薄抹一層。
要是用石灰、石膏、黏土等和在一起,制成水泥修院子,那花銷可不是現在幾貫錢就能打住的。
但饒是如此,幾車從外地運來的石灰也讓在前院忙碌的小夥子們大開眼界,拌石灰砂漿的時候恨不能小心再小心,生怕浪費了丁點石灰。
就連與其他人閑聊時,都會忍不住拿出來講,說許家食肆刷牆的泥漿,竟然要幾百文錢雲雲。
真是大手筆啊!衆人暗自感嘆。
謝虞琛見過工地上的工人們幹活,對石灰砂漿的配比多少有點印象,反正比院子裏那些戰戰兢兢的幫工們熟悉。
次日一大早,他便跟許大郎要了一件舊褂子套在衣服外面,做起了拌砂漿的活兒。
倒不是真要挽起袖子打灰,他再怎麽說也只是個理論派,比不上院子裏這些常年幹活的男郎們熟練。
真刷起牆來速度慢吞吞就算了,萬一刷不勻還得返工重幹,平白給人添亂。
他主要是起到一個教學和示範作用。
謝虞琛一邊拌砂漿,一邊給衆人講解砂漿的配比和操作要點。
衆人雖第一次見這石灰砂漿,但砌牆打灰這些事情總是相通的,沒幾下便掌握了攪灰抹牆的訣竅,幹起活來那叫一個麻利,“唰唰”兩下,一面牆就刷好了大半。
見刷牆的進展快,謝虞琛也高興,揚手一揮便叫人給工匠們今天的中飯裏再加一道肉菜作為獎勵。
聽說今天的飯裏有肉菜,前院頓時熱鬧起來。年輕人的嗓門又大,很快便把謝虞琛吵得又躲回了後院。
往回走時,謝虞看到挂在一旁晾曬的蘿蔔幹也曬得差不多了,便招來兩個在廚房打下手的小娘子,讓她們把蘿蔔幹取下兩挂來,按照自己前幾天教過的辦法,拌一個蘿蔔菜。
最好是能多拌幾盆,等到中午吃飯的時候端到前院,也算是給工人們添一道下飯的小菜。
明明是快要入冬的天氣,院裏幹活的人們頭上卻還在冒汗。
但衆人都不覺得有什麽,胡亂擦了兩把就完事了,心裏還盤算着今天中午的菜色。
若是自己中午省下幾口,将那份肉菜打包回家,還能給爺娘妻兒也嘗個味……
想到這兒,衆人幹起活來就更加賣力了。
許大郎邀來做工的都是些年輕力壯的小夥,正是能吃的時候,這幾日幹得活又辛苦,有時候一頓吃兩碗粟米飯都不是什麽稀罕事。
最開始許大郎還有些憂心,哪有這樣的主人家,請了幫工卻讓他們甩開膀子吃飯的?
就那些人的飯量,豈不是要把家裏的米缸都吃空了
他把這事跟謝虞琛一說,對方卻好像半點不在意似的,只說放開了讓他們吃去,不過是幾升粟米的事情,沒必要看得這麽緊。
這确實不是什麽大事。謝虞琛心想。
那些幫工他大多都打過幾回照面,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小夥子,放在後世怕是還在讀書,正是享受青春熱情,最肆意張揚年紀。
但在現在,卻已經是家中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和頂梁柱。
許家的活辛苦,這在蓬柳村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但因着村人們沒有別的賺錢門路,許家給的那幾文錢在他們眼裏已經是不可多得,每每聽說要招人,都搶着要報名。
他一個人力量有限,能做的也不過是多拿出些糧食來,讓這些人能吃頓飽飯。
因為生活的時代不同,謝虞琛的觀念自然也和衆人不一樣。他不指望現在的許大郎能明白,見對方仍是那副想勸又不敢勸的模樣,便道:
“左右不過是一點糧食而已,現在許家食肆的風頭正盛,沒必要為此和村人交惡。況且那批幫工也都是從前和許家關系親近的郎君。”
許大郎愣愣地應了一聲,不再糾結糧食的事情。
香噴噴的粟米飯冒着熱氣,飯香味飄了老遠。許大郎端着盆走出門,招呼着衆人吃飯。
聽到許大郎的招呼聲,前院的幫工們跑得飛快,沒幾分鐘便在長桌前排做一排,生怕自己來的晚一些,肉菜就要沒了。
開玩笑,這可是尋常人家一年也吃不上幾回的葷腥!
而且看樣子還不是那種切得碎碎的,讓人只聞其味,不見其身的肉沫。而是大塊大塊,燒得熱騰騰的,沾滿醬汁的肉塊。
衆人領了飯,也不講究什麽,随意在許家院子裏尋了一個背風的牆角蹲下,便開始鉚足了勁地往嘴裏扒飯。
見衆人狼吞虎咽的模樣,許大郎覺得自己好像并沒有像他以為的那樣,産生類似可惜或是舍不得糧食的想法。
但他也說不出心裏是什麽滋味,總覺得鼻腔酸澀,好像下一秒便會流下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