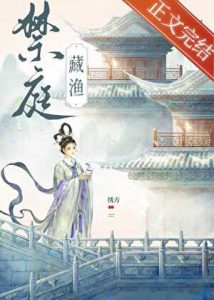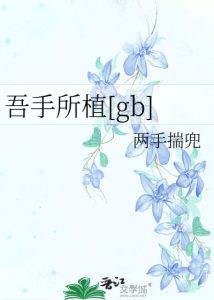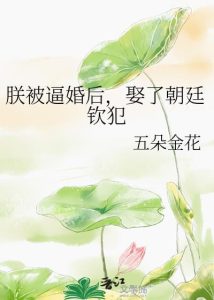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40 章
東山州外新修的一條黃泥路上, 吱吱扭扭行着一輛半新的驢車。坐在驢車上的老翁伸手摸了摸拉着貨的驢子,計算着還有多久才能到達他們村子。
他身後還跟着一個半人高的男娃,是老翁八歲的孫子。祖孫二人都是東山州下屬的畢原村人。
這回趕着驢車去東山州, 不是為了別的, 而是為了把采石場新燒出來的一車水泥拉回村。
将近半月時間的暴雨結束後, 畢原村的田地雖然不幸被摧毀大半,但房舍倒是還□□着。只是免不了嘩嘩地漏着水。
縣裏巡查的官吏見狀, 便寫了一份文書遞到了州衙, 向關泰初那兒詳細彙報了畢原村的情況。
這項定期彙報的規定也是水患發生後才新制定出來的。各個村莊由村裏正搜集受災情況,記錄在冊後再統一彙報給州府,由州府調派糧食、布匹一類的赈災物資。
為了杜絕有人從中中飽私囊,或是有瞞報多報的情況發生,州府還會定期派專人到村裏檢查。
畢原村原本的那個裏正, 就是這樣被罷免了職務, 關進了大牢裏。
舊裏正因為貪污被罷免, 新的裏正又還沒上任, 他們村的情況便由縣裏的官吏直接彙報給了州府。
文書抵達州府後不過三日,便有人通知畢原村人, 說是州府那邊知曉了你們村的情況,給你們批下幾十擔水泥來,供你們修補漏水的屋舍。
只是最近州府那邊人手也緊缺得厲害,所以要麻煩你們自己帶着文書到采石場那邊去領。
村人們當然是沒什麽異議。州府能給他們那些水泥,讓他們修補房屋, 衆人已經是高興得不得了。
現在十裏八鄉的誰沒聽說過水泥的名聲。用水泥修建的屋子不僅一點都不漏水,而且還特別堅固。
想買水泥的人家能從東山州這頭排到那頭。聽說是因為水泥生産起來頗費功夫, 所以一時半會兒才供不起那麽多的客戶。
那樣緊俏的東西官府現在卻直接白白分給他們,村人可不是感激都來不及?
聚在一起一商量, 便決定讓他們村有車的人家,還有那些年輕力壯的後生,挑着擔子、趕着馬車地往采石場去了。
“阿爺,你可累着了?要不換孫子來趕車吧?”
說話的那人正是老翁的小孫,別看他年紀小,但已經能幫家裏割草喂羊,做許多事了。趕起驢子自然也是不在話下。
他們家的家境還算過得去,養了五六頭羊。去年為了去城裏賣肉賣菜方便,咬咬牙買下一頭驢車,也就是老翁現在趕着的這輛。
也正是因為這駕驢車,他們家才被選去采石場運水泥。
“阿爺不累,而且就快到了。”老翁揮鞭在驢屁股上輕輕拍了兩下,嘴裏不忘吩咐自己的孫子:“你且照看着點車上的水泥,這路不平,莫教它們撒出去咯。”
“知道,知道!”小孩的聲音脆生生的,絲毫沒有半點長途奔波的疲憊,“人家都說這水泥珍貴,我一直仔細看着呢。”
“那就好。”老翁伸後手去,粗糙的手掌在小孫子柔軟的發頂撫摸了一把。
他們整個畢原村就指望着這些水泥修補漏水的屋舍呢,可不敢在路上出什麽差錯。
……
東山州還有許多和畢原村一樣的村子,有的受災更嚴重些,有的沒那麽嚴重,但無一例外,都得到了官府妥善的安置。
而那些沒了田地的人家,官府也鼓勵他們到城外的采石場和林場做工換取銀錢。
這個季節遭遇水患,對整個東山州的打擊都是巨大的,更不用說那些靠天吃飯的普通農家。
為了一家人不餓肚子,許多家庭的勞動力都到了林場做工。還好像挖坑培土、栽種樹苗、澆水施肥一類的活計,還難不倒他們這些原本就以種田為生的人們。
不僅是家裏的男性勞動力,只要是家中長輩還能做飯照看孩子的人家,那些媳婦們也跟着自己丈夫到了林場。
那麽大的一片林地,每天燒水做飯也需要不少人。
丈夫在林場裏種樹,她們便做這些燒水灑掃的活計,每日也能賺到六七文錢,養活一家人算是綽綽有餘。
……
一千畝林地栽種了三分之一的時候,謝虞琛帶着人到了林場裏視察。
叫來幾個管事問詢了一番,才知道移種來的杜仲樹苗的成活率還算不錯。可能是因為運輸中照看得周全,一百株樹苗了只枯死了七八棵,比謝虞琛預計中的還要好不少。
種樹這種事謝虞琛不擅長,看到杜仲樹長勢不錯,裏面的工人也都各司其職,工作得安安穩穩後,他便帶着人離開了。
這段時間以來,以工代赈的法子已經初建成效。受災的百姓有六成都在采石場和林場找到了足夠維持生計的活計,官府的工作量大大減輕。
謝虞琛規劃好的杜仲林地也借着這個機會初步建成。
雖然現在的杜仲樹苗還不能帶來收益,但水泥一經面世便廣受歡迎。
不論是普通人家挑一擔半擔回去修補加固屋舍;還是稍微富裕一點的家庭,買了幾車的水泥,和上沙子給整個院子上下都抹了一遍。
至于那些鐘鳴鼎食的世族大家,倒是看不上水泥抹牆後粗糙的手感。畢竟他們原本的府宅就足夠精巧華美。但頂不住用水泥鋪成的路實在是平坦幹淨,也不會一下雨就滿是泥濘。
因着這個,那些世家大族也都買了不少水泥回去,把府宅中所有的路都重新鋪了一遍,花銷一點不比那些用水泥抹牆的人家低。
至于剩下的那些沒有去到林場做工的百姓,也因着水泥的大火,帶動着各行各業都熱鬧起來。
靠着給商隊做腳夫,挑着擔子到附近村縣賣水泥,去食肆客舍幫工等許多活計,雖然辛苦些,但也足夠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
謝虞琛在東山州赈災的消息傳回京城,奏折一封一封地遞到皇宮裏去。
小皇帝也不藏着掖着,每次收到東山州傳回來的奏折,第二天就拿到早朝上當衆宣讀,狠狠打了那些最開始反對烏菏巡視的大臣的臉。
當初反對的聲音有多高,現在臉就有多疼。
最開始就是那些人吵嚷着說烏菏此舉不僅不能起到整頓吏治的效果,反而會勞民傷財。而且沿途官員接待烏菏,還會耽誤地方政務的處理。
但烏菏定下來的事哪有那麽容易更改。這些人天天跳着腳反對,也不影響烏菏出京的車駕日漸備齊,只能隔三差五地就往皇帝那兒遞奏折彈劾。
小皇帝被他們念叨得煩不勝煩,最後只好把烏菏叫過來,讓他自己處理他惹出來的麻煩。
最後也不知道烏菏用了什麽手段,總之小皇帝再見到那幾個大臣時,對方就安分了不少,也不再提烏菏巡視一事了。
烏菏雖然沒把朝中反對的聲音放在眼裏,但也沒料想會發生現在這種情況——
他這次出京為了探查綏桐一事,巡查本來就是個幌子,自然沒想過能做出什麽政績來。
反正他身上的罪名是虱子多了不嫌癢,多一個勞民傷財也沒什麽影響。
誰能想到這半路跳出一個假扮大巫的謝虞琛來,帶着人二話不說就跑到了那窮山僻壤的東山州,在半月後的水患中給京中交上了一張再漂亮不過的答卷。
消息傳回京中,即使是再看不慣烏菏的大臣,都不得不承認他此舉沒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
別說是治理水患的各項舉措無一不是合情合理,就連當地的經濟都連帶着發展起不少。
他們就算是想在雞蛋裏挑骨頭,也找不出一點問題來。
這幾天的朝中,平常最愛找事的那幾個大臣一反常态地安靜了不少,不再像條瘋狗似的逮着誰咬誰。
平常沒少在他們那受氣的官員只覺得連空氣都輕快了幾分,光是看到那幾人吃癟的模樣,衆人就覺得通體舒暢。
烏菏雖不在京城,但京中的情況卻都被人一五一十寫在了密信中,暗中送到了綏桐。
此刻的烏菏一身圓領缺胯袍,頭上是硬角幞頭。裝束和大街上的那些普通儒士沒有半分差別。
如果不是舉手投足間流露出來的冷肅之意,旁人還真看不出他是那位威名赫赫的巫神來。
将手中的信箋随手丢到幾案上,烏菏輕笑一聲,自顧自感慨了一句:“能讓那些老東西們服氣,也是不容易。”
一旁的內衛揣摩着他們大人的心思,緊跟着應和道:“這幾天大人您有所不知,謝郎在東山州的所作所為都傳遍京城了,就連那些世家見了那什麽水泥鋪成的路,都贊不絕口呢!”
“他們倒是識貨。”烏菏道。
水泥面世沒多久,烏菏這裏就收到了周洲的消息,嚴格算起來比那些世家大族還要早。而除了那份詳細描述了水泥燒法的書信,一起寄來的還有一塊巴掌大的水泥塊。
雖然沒有親眼見到水泥是如何和好,如何經過晾曬後慢慢變得和石頭一樣堅硬,但光是看到那封信,烏菏心中就足夠震撼了。
當時站在一旁的內衛颠了颠手上的石塊,也忍不住內心的驚駭之情,張着嘴感慨道:“從前只聽百姓中流傳着什麽‘點石成金’的奇聞,卻不曾想屬下竟親眼見到了這‘點土成石’。”
而且就按現在水泥的受歡迎程度,某種情況上,謝虞琛此舉也和點石成金差不了多少。
試想一下不過是一些最普通不過的黃土和石灰,混合起來經過煅燒後竟然就能變成這般神奇的物件。
從前他們建房修路,不知要費多少工夫和銀錢才能建成。現在直接把這水泥和砂石添水攪和勻,平平地鋪在地面上或是磚瓦之間,就能輕而易舉地建成屋舍和道路,而且建成後風吹不倒,水澆不壞。
衆人圍在一起,盯着桌上那塊質地粗糙的水泥塊看個不停,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什麽金玉之類的寶貝呢。
想起這幾天莊子裏衆人為了一塊水泥的癡迷模樣,烏菏忍不住勾起唇,露出一個微不可察的笑來。
一旁的內衛見狀,還以為是自己剛剛的奉承起了作用,連忙堆着笑又道:“大人您有所不知,現在許多百姓都誇贊您,說您是當之無愧的……”
“誇我做什麽?”烏菏皺着眉打斷了內衛的恭維。
內衛一愣,小心翼翼地解釋道:“這……自然是因為您在東山州赈災有力,讓百姓們沒有因為水患而流離失所……”
烏菏的眉頭越皺越緊,內衛也逐漸意識到了不對勁,說話的聲音逐漸低下來,神态也不像最開始那般眉飛色舞的模樣。
“在東山州赈災的是周洲和謝虞琛他們,還有當地的官員,和本巫有什麽關系?”烏菏不悅道。
內衛一時間摸不清楚他的意思,不清楚烏菏是為何生氣。
斟酌半晌,大抵是覺得他們大人的模樣不像是因為謝郎在東山州搶了自己的風頭而發怒,才小聲解釋道:“但百姓又不知道巡視的那位不是大人真身。”
聞言,烏菏曲起手指輕扣着桌面,但緊皺的眉頭卻是漸漸松開了。過了一會兒,才又開口吩咐道:“去拿紙筆來。”
寫好的信用封蠟封好口,再由人快馬加鞭地送去了東山。
等信件送到謝虞琛書案上時,他正和畫師一起琢磨橡膠草的畫法。
“這種植物長相與蒲公英相似,但時葉片比蒲公英的葉片要更厚實。”
“邊緣有波浪形的缺口,對,這裏要再圓潤些……”
雖然有了杜仲樹,但如果可以,謝虞琛還是想把性能和天然橡膠更為相近的橡膠草找出來。
無奈他本人也只是偶然在圈內一位熱衷于搜集各種植物的大佬那裏見過一回橡膠草,對它的模樣僅僅有一個大致的印象。
而他本人的畫技又一般,經過自己口頭敘述和畫師下筆畫出來的橡膠草,要麽是這裏不太像,要不是那裏不對勁。整整一天都沒畫出謝虞琛想要的模樣。
“這是,給我的信?”謝虞琛接過周洲遞來的書信,面露疑惑。低頭看過去,信封上的火漆烙印确确實實是烏菏的印章。
揮退早已膽顫心驚的畫師,謝虞琛滿心疑惑地拆開了手中的信件。
信件并不長,滿打滿算只有一頁半的內容。細薄光潤的紙張看起來就知道價值不菲,但最吸引謝虞琛目光的還是這紙上的字跡。
他前世曾經接過一個羽扇綸巾的名士角色,為此還苦學了幾個月的書法。只是原本是為了演戲需要,後來卻因此愛上了書法。
眼前的字跡他一眼便能看出不凡。
紙上的字跡不像是謝虞琛的那一手字,有着風流飄逸的潇灑。
如髹漆一般黝澤可鑒的墨字,一橫一豎透露出來的,是一種冷冽剛直的肅殺之氣。
……像極了那個玄衣銀發,輕笑着便用最殘忍的方式解決掉數十個刺客的男人。
謝虞琛捧着信箋仔細端詳了一會兒上面的墨字,才默不作聲地看起了信裏的具體內容。
信上的內容倒是不複雜,言簡意赅地交代了幾句綏桐的情況,告訴自己他不日之後便可離開此地。
除此以外,還稱贊了他之前送來的水泥,字裏行間能看出來烏菏對此物頗為重視。
雖然烏菏會給他寫信是謝虞琛沒有想到的,但裏面的內容卻是十分尋常,唯一讓謝虞琛感到意外的只有最後半頁的內容。
信件的最後,烏菏提到了這幾天在朝中傳得沸沸揚的赈災一事。
将信箋折好放回到信封裏,謝虞琛面色有些複雜,低頭不知感慨了一句什麽,引得一旁的周洲好奇地把脖子伸得老長。
倒不是什麽大事,只是謝虞琛沒想到烏菏竟然會注意到這種細枝末節。
信裏的最後的內容大抵是:此次赈災,謝虞琛付出良多,最後卻是讓他平白得了那麽多好處。就連百姓争相贊頌的,也都是他這個什麽都沒做的人。
但頂替他身份一事一旦讓人得知,怕是後患無窮。
名譽沒有辦法還給謝虞琛這個真正為災民做了事的人。烏菏心中有愧,便提出讓謝虞琛提一個要求,只要自己能做到,就一定竭力完成。
言辭之間頗有一種“無功受祿,寝食不安”的無措感。不像是那位權朝傾野的年輕大巫,反倒像是個無緣無故得了一大把糖果的半大稚子。
“倒不知你們素來威名赫赫的巫神大人竟然還有這樣一幅模樣。”
謝虞琛輕笑一聲,沒頭沒腦地來了這麽一句,惹得周洲對信裏的內容更是好奇。
可無奈他們大人既說了這份信是給謝虞琛的,周洲就是有一百個膽子,也不敢偷看裏面的內容,只能在一旁好奇得抓心撓肺。
“這信需要‘閱後即焚’嗎?”謝虞琛心情好,說話的語氣便也帶了幾分輕快。
周洲聞言,猶豫了一會兒才道:“若是信裏沒什麽別的內容就不用……”
謝虞琛微微颔首表示明白。信裏數次提到他假扮巫神一事,不用想也知道是不能留的。若是被有心之人得了這封信,恐怕會有不小的麻煩。
他嘆了口氣,有些不舍地摩挲了一下信封上的火漆印,最後還是遞給周洲道:“以防萬一,你還是拿去燒了吧。”
可惜了那樣漂亮的兩頁字。謝虞琛心道。
倒不是說烏菏在書法上的造詣有多麽高,讓人不忍損毀。只是字裏行間那種淩厲的風骨,即使翻閱過許多名家字帖,謝虞琛也依然覺得極為罕見。
見字如見人,古話倒是誠不欺我。謝虞琛搖了搖頭,靜靜看着火舌逐漸将那封薄薄的信箋給吞噬得一幹二淨。
“公子,綏桐的情況怎麽樣?”周洲小心翼翼的詢問聲打斷了謝虞琛跑遠的思緒。
自烏菏換船離開,他跟着謝虞琛來到東山州,到現在已經将近三個月過去,這還是第一次收到他們大人傳來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