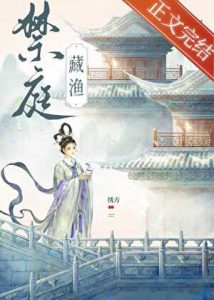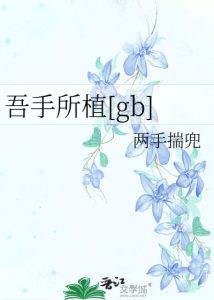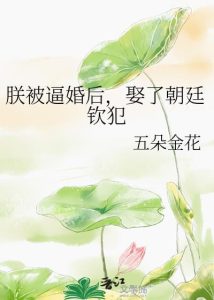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39 章
“回大人的話, 水位确實有所上漲,下官已經命人開渠引水,附近村縣暫時還沒有災情發生, 但是……”
像是不知道接下來的話該怎麽說似的, 關泰初的聲音越說越低。
“但是什麽?你且說無妨。”謝虞琛道。
“是這樣, 雖然百姓的房舍暫時沒有受損,但是大人之前視察過的那家采石場……昨天卻發生了塌陷事故。”關泰初面上露出了一抹複雜的神色。
東山州降下這麽大的暴雨, 發生水患已經是衆人預料中的事。關泰初這幾天一直在帶着人開渠、運糧, 萬一真發生洪災,也好有個準備。
誰知道這雨水偏偏就把仲家的采石場給沖垮了一部分,還是巫神大人視察過的那個。
這消息一出,城中議論紛紛,都猜測是不是那家采石場平日裏欺壓百姓犯下罪孽, 惹得巫神大人心生不悅, 于是上天才降下災禍, 以示懲戒。
對上關泰初複雜中帶着一絲探究的目光, 謝虞琛茫然了一瞬,才反應過來對方是在懷疑采石場的坍塌與自己有關。
聯想起這幾天周洲彙報給他的那些個市井傳言, 謝虞琛更是有些哭笑不得。
他要有這本事,哪還用天天擔心尋不到後世的那些作物,和上天溝通一下,立馬便能知道那什麽橡膠草、棉花之類現在的藏身之處。
白了關泰初一眼,謝虞琛才又問道:“那礦場可有人受傷?”
沒想到, 聽到這話的關泰初面上表情複雜更甚,“……回大人, 除了當時正在礦場內的仲翰海被掉落的石塊砸傷了手臂以外,再無其他人受傷。”
“……挺好的。”謝虞琛嘴角一抽。
嘶, 怎麽好像更解釋不清了。
仲翰海便是那仲學文的子侄,也是他視察的那家采石場的場主。
只有這一家礦場受災,唯一受傷的人又是謝虞琛看不順眼許久的仲家人。
也不怪城中會傳出這樣的流言,若不是謝虞琛自己就是當事人,他指不定也會嘀咕幾句。
謝虞琛不甘心,還在試圖從科學的角度為自己辯駁幾句——
“采石場開設數年,開采不規範導致岩體本身的平衡受損,或是因為越界開采,将底部給挖空了。”
“這樣一來,一旦有暴雨沖刷,便很容易發生滑坡坍塌的事故。”
至于為什麽只有仲翰海一人受傷?
自然是因為這幾天仲家人夾着尾巴做事,一看到謝虞琛讓官辦的采石場停止開采,注意安全,立馬便跟着停了工。
只有仲翰海心裏不忿,又不敢公然反抗仲學文的命令,便悄摸帶了人跑到礦場,計劃偷偷複工。
因為要瞞着衆人,他自然不可能帶着一群下屬浩浩蕩蕩地去視察,選的地方也比較偏僻。
這樣一來,采石場發生事故,石頭恰好砸到他身上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所以,雖然巧合了點,但這确實和他謝虞琛沒有半點關系。
當然也和什麽天罰無關,純粹就是那仲翰海自己倒黴。
“周洲你聽明白沒有?”謝虞琛看向一直在假裝不存在的周洲。
“屬下明白。”周洲點頭應道,表情認真,沒有半點破綻。
“那關大人你呢?”謝虞琛又轉頭看向另一個。
“下官……也明白。”只是聽這語氣,好像“明白”得并不情願就是。
***
因為有提前準備,即使暴雨陸陸續續下了大半個月,官府還不至于手忙腳亂。關泰初也帶了一衆官員四處修建防洪堤,開倉赈災。
雖然這其中也發生了幾起暴雨沖垮屋舍農田的事件,但因為處理及時,沒有造成人畜傷亡,已經是盡可能地将損失降到了最低。
再加上東山州有謝虞琛坐鎮,百姓雖然畏懼這位兇名在外的巫神大人,但這種時候有他在城中,反而會覺得心安。
謝虞琛時不時帶着人探查災情,巡視倉廪,也隐隐表達出一種“巫神與百姓同在”的意思,無聲安撫着百姓。
因此雖有水患威脅,但整個東山州還是比較穩定。
從城郊臨時搭建的棚子回來,已是暮色蒼茫,謝虞琛倚在馬車內的引枕上,疲憊地按了按眉心。
“根據水則碑的記錄,這幾日的水位已有了下降的趨勢,估計用不了多久,洪水便能徹底退下。”周洲點了一支安神的香,寬慰道。
水則碑就是建在河道湖泊旁用來觀測水位的石碑,由幾根堅實的石柱組成。通常一邊用來記錄歷年來的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可以和另一邊的實時水位進行對比,方便記錄者及時觀測水位的變化。
根據這幾天記錄的結果來看,水位已經隐隐有了下降的趨勢,再過幾天應該就能恢複正常的水位高度。
聽到檢測官彙報的時候,謝虞琛也是舒了一口氣。
這段時間關泰初帶着一衆官員指揮救災,他也沒歇着。
像是安撫民心這種事,關泰初出面就不如謝虞琛的效果更好,更有說服力。因此,這幾天謝虞琛幾乎将東山州所有受災的地方都巡視了一遍。
天氣雨多晴少,道路又泥濘,路程的艱辛可想而知。不過效果也是顯而易見。
這半個月裏,哪怕是條件最艱苦的時候——常平倉的糧草不夠,調度的糧食又因為暴雨延誤了幾日。赈災的糧食短缺,東山州也沒有發生任何暴動,或是類似民變一類的不安定之事。
災民們都堅信謝虞琛和官府不會放棄他們,甚至還自發組織百姓維護起城中的防務。
“等到水患結束,公子打算如何處置城外那些臨時安置的百姓?”
這段時間跟着謝虞琛四處赈災,對方的一言一行衆人都看在眼裏。
關泰初等人或許沒什麽特別的感受,最多覺得對方并不像傳聞中的那樣兇殘暴虐。畢竟他們都以為眼前的人就是那位位高權重的巫神大人。
但周洲等人心裏卻清楚得很,現在被萬人敬仰的巫神,其實和他們大人沒有半文錢關系,而是一個出生不詳、渾身透露着神秘的人。
這段時間,謝虞琛安撫災民是并不是一味地表現出和煦寬容之态,而是恩威并濟,既能讓百姓踏實,又能震懾到其中心術不正之人,讓他們不敢妄動。
這其中的尺度拿捏得正好,就好像他生來就知道應該如何去做似的。
包括周洲在內,謝虞琛身邊的內衛對他的态度都在悄然發生着變化,這點謝虞琛看得清楚。
沒辦法,中華歷史上下數千年,那麽多有參考價值的事例和人物擺在那裏,他只要用心去看。
學習、模仿、因地制宜、融會貫通……
現在謝虞琛治理起東山州水患,不說是得心應手,那也算是有模有樣。
周洲本人對謝虞琛的态度,相比起在寶津渡的時候,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在船上的時候,連窗戶壞了他都只當做沒看見,直到烏菏吩咐才不情不願地派人去修。
但現在,別說是窗戶,謝虞琛揉一揉眉心,周洲那邊安神香就已經點上了。
遇上謝虞琛視察粥棚、安置點時,不管對方什麽時候回到馬車上,周洲都煮好了一壺冒着熱氣的姜湯等着他。雖然味道一般,但驅寒暖胃的效果卻極好。
……
這樣周全的安排平日裏更是随處可見,要不是周洲在面對內衛時仍是那副橫眉豎眼的模樣,內衛們都懷疑他們的首領莫不是被什麽鬼魂狐妖的給奪舍了。
真是奇哉怪哉。
周洲本人卻不當回事,俨然有從“烏菏毒唯”發展成為“謝虞琛死忠粉”的趨勢。
接過對方遞來的熱毛巾,謝虞琛抹了一把臉,慢吞吞地說道:“房舍重建還需要一些時日,況且東山州的財政實在不豐,土地又貧瘠,組織百姓開墾荒田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見到成效……”
伴随着謝虞琛的分析,周洲的眉頭也跟着皺了起來。
他心道:公子說得對,赈災只是一時的,災後如何重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暫時的想法是以工代赈,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什麽好的計劃。”謝虞琛看向周洲。
畢竟在這方面,他本人算是外行,周洲常年跟在烏菏身邊,應該見過不少類似的事情,比他更有經驗才對。
“以工代赈倒是不錯……”
周洲沒想到謝虞琛會突然問起自己的看法,愣了片刻才斟酌着開口道:“豐慶九年,安梁府發生水患,大人也是用了這個辦法。”
“哦?”
現在是慶豐十三年,也就是說早在四年前,烏菏也才是個十九歲的少年郎,便已經擔此重任了嗎?
謝虞琛起了一點興致,坐起身子看向對方,“你仔細講講?”
周洲點了點頭,回憶着當時的情況,悠悠開口:“當時大人奉命前往安梁……”
“前安梁府尹趙思誠貪污朝廷調撥的救濟銀,隐瞞謊報災情。等到大人到達時,整個安梁已是餓殍載道,平地水深數尺,城外一片汪洋。”
回想起當時的場景,即使數年過去周洲還是心有戚戚。
地勢低窪的地方全部被洪水洗刷過一遍,近乎十室九空。
好不容易躲過水患的百姓又拿不到赈災的糧食,什麽易子而食之事,更是時有發生。
路上遍地都是屍骸,有被水淹死的,有生生餓死的,還有因為起義被官府打死的流民。
無人掩埋的屍體腐爛生蛆,引來蠅鼠啃食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随之爆發的疫病。
……
用“人間煉獄”四個字形容都不為過。
直到烏菏帶着糧食、草藥和郎中抵達了這片暗無天日的地方。
茫茫苦海,烏菏玄衣纁裳,銀發如瀑,如神祇降世。自此晨光破曉,一片燦然光亮。
謝虞琛雖然不曾親眼所見,但也能根據周洲的描述想象到那個畫面。
對于安梁的百姓來說,不論烏菏在別人口中是如何殺人如麻、暴虐無道,但在他們眼裏,烏菏就是無邊黑暗中的第一抹希望。
“再然後呢?”
周洲略過那幾個月不眠不休地操勞,又講起平複災情之後的事來。
“等到災情被控制住後,安梁的一衆官員也都已斬首,大人便開始安置流民。當時大人也說了和公子一樣的話,說要以工代赈。”
“除了官府興建堤壩、開挖水渠以外,大人還召集起當地的世家,告訴他們以如今的境況,許多流民無家可歸。若是借此機會修建祖宅祠堂,只需給他們提供飯食住處,便可雇傭他們做工。”
世家大族傳承百十年,家底豐厚,赈災時也沒少出錢出力,這也是烏菏願意坐下來和他們心平氣和談話的原因之一。
将城中的災民轉化為勞動力,官府和世家能節省成本,百姓也能暫時以此謀生。這是當時最有效的辦法,安梁也因此渡過了這場危機。
後來官府組織他們開荒,又将一部分百姓轉移到田地充足的地方,那就是再往後的事了。
“就算是這樣,朝中還有人彈劾大人,說國庫本就不豐,赈災的銀錢都是好不容易才調撥出來的,大人卻大興土木,無疑是在勞民傷財。”想起朝中當時反對的聲音,周洲撇了撇嘴,下意識替他們大人打抱不平。
見周洲語氣忿忿,謝虞琛笑了笑,也對烏菏當時的舉措表示了贊同:“你們大人當時做得很對。若不是鼓勵興建土木,一時無處安置那些災民,花費更大不說,也容易再生事端。”
周洲頓時由怒轉喜,想起東山州的近況,又轉口道:“可惜東山州一帶的富商豪紳不多,不然公子也能從他們那兒敲打出點銀錢糧食來。”
當時的安梁,屯糧賣高價的糧商可不少。若不是烏菏手段強硬,雷厲風行地處置了一批屯糧的無良商賈,安梁的糧價還沒那麽快能穩定下來。
“東山州又不像安梁一樣,有許多屯糧賺取不義之財的商賈。”謝虞琛失笑。
不僅如此,許多人還主動捐贈給官府糧食布匹,共同抵禦水患。
就連仲學文,都不知道是因為信了坊間關于仲家罪孽太多,惹惱上天降下神罰的傳聞,還是不願觸烏菏的黴頭,竟然也主動捐出了将近二十斛,也就是兩千多斤粟米。
這樣一來,他就更沒有理由對他們下手了。
也不知道好好一個朝廷官員,周洲這一身的匪氣是從哪學來的。
聽到謝虞琛的話,周洲更是露出一抹可惜的神情,“東山州也沒什麽大的世家,公子就是想鼓勵他們修葺祖宅祠堂,恐怕也分擔不走幾個災民。”
“是這樣。”謝虞琛點頭。
所以他們還是得另尋出路啊。
“可惜杜仲樹不能在這個時節栽種,不然問題就解決了。”周洲感慨了一句。
官辦的采石場和水泥生産那邊已經招攬了足夠的工匠,其中許多是從仲家的采石場那裏來的苦工,顯然是不可能騰出更多的位置用來安置災民。
官府財政告急,也拿不出那麽多銀錢雇傭百姓興建土木。
若是謝虞琛規劃的杜仲林地現在開工,倒是能解決掉災民安置的問題。
謝虞琛思考了一整晚,最後還是決定冒險一把。若是順利,把時間恰好卡在夏末秋初的季節,說不定杜仲樹也能成活。
“殿下若是覺得可以,屬下就去吩咐那汪家藥鋪的掌櫃。”周洲自然不會反駁謝虞琛的決策,當即便要排人去去找汪淳商定此事。
謝虞琛思慮再三,最後還是點頭放行。
東山州現在最缺的無疑是堤壩水渠一類的水利設施。但這類大型工程的耗費,可不是一座采石場,一片杜仲樹林可比的。
不過現在水患已消,采石場那邊的水泥很快便能開始投入生産。若是順利,只需再過半月便能見到收益,彌補州庫的虧空。
等到州府的財政豐盈起來,便有錢興修水利、改良水土……
總之,前途還是比較光明的。
這幾日,謝虞琛主要忙碌的便是杜仲林地開辟一事。
許多災民都被雇傭到林地去,為杜仲樹的移植做着前期準備。
汪淳的消息也快馬加鞭地送往了秦嶺一帶。一千畝的杜仲樹可不是一個小數目,起碼要分好幾批送達。
除了汪淳聯系的那幾隊和他相熟的商隊以外,許多消息靈敏的本地商客也組織了人馬進山開挖樹苗。
反正除了和汪淳簽訂協議的那部分以外,謝虞琛又沒說必須得是哪家商隊送來的樹苗才行。大家憑本事搶飯吃,自然是先到先得。
這種競争環境下,就連拿到白紙黑字協定的商隊都有些着急,生怕那些人到得比他們早。
到時候東山州那邊缺不缺杜仲樹苗還是其次,萬一惹了巫神大人不滿,他們以後可別想在南诏做生意了。
這一來一去,各個商隊更是碼足了勁兒開挖樹苗。日夜兼程地趕路不說,還有人把心思放在樹苗的成活率上。
樹根上的土,往多了帶!
遮陽的深色篷布,往厚了碼!
就連給樹苗身上灑水,都一個比一個勤快。
這樣瘋狂的競争,結果就是謝虞琛不僅提前半個月就迎來了商賈的車馬,上面運送着的杜仲樹苗看起來也還是生機勃勃的模樣。
移植的成活率應該不會低,謝虞琛心中确信。
就在以關泰初為首的大小官員翹首以盼的杜仲樹苗運來前,采石場那邊的生産也步入了正軌。
生産出來的水泥一進入市場,就受到了人們熱切的歡迎。
最先用上水泥的,是距離東山州往北十幾裏外溪陽縣的幾戶人家。
溪陽縣所處的偏高,倒是沒受到水位上漲的影響。
最開始溪陽縣的人還在擔心東山州治理不利,會有流民逃難到他們這裏。觀望了數日後,發現并沒有從南面逃來的難民,城中百姓才舒了口氣。
倒不是他們冷血無情,主要是這種大批的流民他們也沒地方安置。一旦處理不當,極有可能發生類似哄搶糧倉一類的惡性事件。
萬幸東山州府把水患處理得很好,流民也都安置妥了。
但溪陽縣雖然沒有等到來自東山州的百姓,卻迎來了挑着擔子的腳夫貨郎。
城門口,有人跟貨郎打聽着他擔子裏的東西。
“此物名叫水泥,和上水和砂石,既能用來鋪路,還能用來修補房屋、黏合石磚,用處可多着呢。”
貨郎急着送水泥,簡短地說了幾句後便告辭離去,留下問話的那人一臉疑惑,半信半疑地念叨:“這水泥當真有他說的那麽厲害?莫不是在唬我呢?”
但很快,溪陽縣的百姓便見識到了這水泥的效用。
許多人從貨郎那兒買回水泥後,就堆在地上,再加上砂石和水和成泥漿,然後用一塊四四方方的板子舀起來往屋頂、牆壁、地上塗抹。
說來也是神奇,那土灰色的泥漿抹到牆面上,竟然也不往下掉。沒過幾天晾幹後就變得堅硬無比。
摸着雖然有些粗糙,但那牆壁卻再也不往下掉灰,屋頂也不漏水了。
這幾天,凡是用了水泥抹牆的人家,門口總要聚起幾個親戚鄰居,圍在一起琢磨這水泥。時不時還要上手摸一把,粗糙堅硬的手感更是讓人忍不住啧啧稱奇。
“我聽許多南方來的貨郎說,江安府的那些富貴人家,喜好用石灰和着砂漿粉刷牆面,外面還要再抹一層石膏。這樣砌出來的牆面潔白光滑,且防水保溫。但我看這水泥抹出來的牆面也不差他江安府的石灰砂漿差。”
“可不是嘛,要我看那石膏還是有錢人家的東西,把牆弄得灰灰白白的,豈不是一下子就髒污了?倒不如這水泥抹牆,又結實又便宜。”
“是嘞,我問過那東山州來的貨郎,這麽一擔水泥才只要二十文錢,若是只抹抹院子啊,兩三擔就夠了,也不費什麽錢。”
衆人一聽這個價格,頓時便有些心動。水泥的效用他們親眼見過的,比那黃泥、土石的要好得多,而且也就幾十文錢,确實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