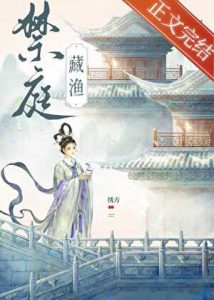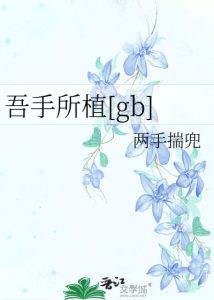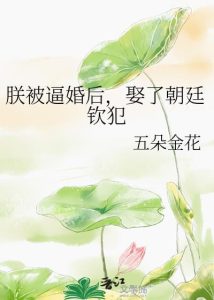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101 章
一衆商販在街上扯頭花似的互相辯駁了起碼有半刻鐘, 才遴選出五個“優勝者”來。跟鬥勝的大公雞一樣,挺着胸脯揚着腦袋,邁着自信的步伐坐上了路旁的人力車。
遮陽的篷布拉下來, 一身短打的車夫抖了抖肩膀, 扭頭囑咐了乘客一句“郎君您坐穩咯”之後, 便将車把提起,躬身邁開步子, 在水泥路上撒腿奔跑開來。
“嘿呦, 慢點慢點!怎麽跑這麽快啊!——”
“看路——,旁邊來人啦!”
遠處傳來幾人撕心裂肺地吶喊,剩下沒擠上第一批試坐人力車人站在路邊,發出了歡快而無情的嘲諷大笑。
讓你們跟我搶!現在麻爪了吧?
其實人力車跑起來的速度并沒有那麽誇張,起碼比全力奔跑起來的馬匹差遠了。衆人做上去後之所以如此驚慌失措, 主要還是因為都是第一次坐, 而且坐騎還是他們從來沒見過的東西。
再怎麽相信謝虞琛, 一旦車子跑起來後還是覺得心裏沒底得很。
衆人排着隊, 每人都被車夫拉着在水泥路上跑了幾圈。最開始的慌亂過後,倒也都承認了這人力車的精妙之處所在, 聚在一起商量,都覺得這項生意大有前途。
“只是……這城中但凡是能消費得起的人家中,大多已經有了馬車作為代步,即使謝郎的人力車比馬車舒适,大多人恐怕也難在一時之間改變自己的習慣。”
相比起馬車, 人力車倒是省了馬匹牲畜的費用,但人家都能坐得起馬車了, 還會在乎便宜的這三瓜兩棗嗎?
這倒是一個擺在衆人面前的現實問題。在場的商販都是個頂個的精明人,一時間都冷靜下來, 齊齊看向謝虞琛,等他給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
“我想諸位可能想錯了。”謝虞琛不疾不徐地開口:“人力車出現在市面上,絕對不是為了與馬車競争,和對方搶占市場。”
“哦?還請謝郎仔細說說。”
衆人一臉不解,謝虞琛卻不答反問道:“請諸位回想一下,大家一般是什麽時候會乘坐馬車?或者換句話說,如果各位只是從自己家到街邊的食肆吃飯,會選擇乘坐馬車嗎?”
衆人面露沉思,片刻之後才三三兩兩地開口:
“如果只是去街上,我一般不會乘坐馬車,坐轎子就行。馬匹要找地方安置,馬車也不能就在路邊停着,不僅麻煩,而且還不方便。”
“我不僅不愛坐馬車,連轎子我都不甚喜愛。我和我弟弟每日去自家鋪子裏,來回都是走路。說不累是不可能的,但這麽多年也習慣了。”
“我同你們不一樣,我經常要在東山州和安葛縣之間往返,帶着那麽多的行李,不能不坐馬車,雖然颠簸,但好歹不用風吹雨淋不是?”
……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地開口,雖然說話的內容各不相同,但大體都是一個意思——
如果是距離比較遠的行程,不管是舒不舒服,基本都是要乘坐馬車的。但若是距離比較近,大家的選擇就多了起來。有選擇騎馬的,有習慣步行的,也有樂意坐馬車的。
謝虞琛目光瞥向拉着衆人坐車感受了一圈後就默默縮在路邊被大家忽視掉的車夫們,對衆商販道:
“可能大家也發現了,這個車子畢竟要靠車夫的人力拉動,所以去不了太遠的地方,而且座位也只能乘坐一到兩個人,局限性還是比較大的。”
衆人目光灼灼地盯着謝虞琛,等着他接下來的轉折。
“但是,人力車的優勢也非常明顯,坐在上面舒服,價錢便宜,而且相比于馬車龐大的體積,也更加靈活。”
衆人贊同地點了點頭,謝虞琛繼續說道:“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城郊見過租賃馬匹和馬車的車馬行?”
“自然是見過的。”人群短暫地沉默了片刻,然後便響起幾句心領神會地長“哦”聲。
在場的衆人都是在商場上浸淫多年的老狐貍,一點就通。聽到這兒,大部分人已經明白了謝虞琛的話裏的意思。
他想表達的內容很簡單,都看過那本著名的《駱駝祥子》吧,裏面的“人和車廠”都沒忘吧?
裏面的人力車散布在城市的各處,只要招招手,花上幾毛錢,就能坐上人力車到達目的地。
那個時候甚至都已經有了電車和汽車通行,馬車都快成舊時代的産物了,都不影響人力車穿梭在城市的每條大街小巷。
更不用說在現在這個年代,人力車絕對是拳打馬車牛車,腳踢小轎步辇的存在。
三月的京城天氣已經開始日漸回暖,街市上也出現了穿着薄衫的年輕郎君。
臨水的茶鋪中,一個年輕郎君招手喚來了店中的小厮,低聲吩咐了他幾句不知道什麽,小厮麻利地甩甩胳膊,轉身跑了出去。
過了一會兒,年輕郎君和同桌的夥伴結賬走出茶鋪的時候,已經有四輛嶄新的人力停在門口。
剛剛和小厮說話的那人把同伴都依次安頓上車,目送他們離開後,才坐上了最後一輛車子。
簡單吩咐了一句“去城東的興襄書院”,便倚着一側的扶手,仰面合上雙眼,閉目養神。
去年剛入冬的時候,不知道從哪流行來開的人力車風潮就率先刮到了京城。
京城畢竟是政治中心,世家大員聚集的地方,不僅富庶,風氣也最為開放,對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強。
第一輛人力車剛出現在京城,就有那好奇心強的郎君,從随行的小厮那裏摸來七八文錢,坐在上面讓車從東市一路拉到了西邊的明春門,這才意猶未盡地停下。
“你這車子不錯,以後就到我府上專門負責接送我吧,我讓我阿父一個月給你這個數,怎麽樣?”那郎君伸手比了一個數字,在用布巾擦汗的車夫面前晃了晃。
人力車能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風靡整個京城,衆人一點都不意外。不管是誰,只要試着坐過一次人力車後,毫不例外地,都會被它的舒适程度折服。
坐過一次平穩舒适的人力車再回去坐他們原來的小轎馬車,在車廂裏被晃得東倒西歪的時候。
就如同吃過山珍海味的人再回去吃糠咽菜;
住過豪宅名邸之後再去睡茅草屋;
穿過杜仲膠底靴之後再去穿麻草鞋;
……
都是完全不可能回頭的事情了。
更何況謝虞琛為了推廣人力車,最開始的定價就定得偏低了點。利潤雖然還算有的賺,但賺得每一枚銅錢基本都是辛苦錢。
賣出一輛人力車的利潤,勾勾算算下來,甚至還不如賣一沓杜仲膠底賺得多。
人力車稀薄的利潤自然也引起了其他人的不解,紛紛出言勸說謝虞琛把價錢定得高一點。
“以人力車的受歡迎程度,謝郎即使在現在的價錢上加個七八十文,都不愁賣不出去。”
但基本都被謝虞琛給回絕了。
“人力車越快進入到世人面前,東山州産的車輪和各種零部件才能越快打出名頭。我們要賣的不僅是幾十上百輛人力車。”
“杜仲膠制成的車輪、滾珠軸承才是将來利潤的大頭。”
從東山州運往各地的人力車都是小數目,像東山州這樣的城市,可能只需要百十輛人力車,百姓的出行需求就達到飽和了。
誠然,人力車也會年久損壞,也會需要更換車輪。但相比起整個國家的全部馬車,長途奔馳更容易磨損的車輪……這部分才是他們未來選定的主要市場。
雖然賺得錢少了點,但正是因為謝虞琛把人力車的價錢降到了最低,不管是京城還是其他地方,人力車才會以雷霆般的速度迅速占領市場,在各地站穩了腳跟。
馬車的生存空間倒是并沒有被人力車擠占掉多少,畢竟馬車主打的是遠距離的出行。人力車再怎麽輕巧方便,遇上要出遠門的顧客都得乖乖往後稍。
在京城,因為人力車的出行而大受波及的,首要的是那些擡轎的轎夫。
轎子在速度上跟人家沒法比就算了,關鍵還沒人家舒服,也沒人家省錢。擡一頂轎子最少最少也得兩個人。許多甚至要四個人。
但人力車呢,只要在前面站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拉着車把就能滿城地跑,關鍵是這麽一趟下來,竟然比他們兩個人擡一頂轎子的還要輕松一些。
真是人比人氣死人啊。最關鍵的是,人家人力車在管理上也超了他們好幾條街。
人力車剛開始在京城興起的時候,官府就下發了文書,據說叫什麽……人力車管理……規範條約什麽的。那文書具體叫什麽名字他們記不清,但裏面的內容他們可是記得的。
文書裏第一條,就規範了京城裏所有人力車的主要行駛路線和應收的價格。
規劃出來的幾條線路都是京城的主幹道。每一條路還會劃分路段,比如從東市出來,到宜蘭寺就是一段的路程。每一段路程大概以一裏左右的距離劃分,按照路段收取費用。
除了距離以外,雨天或者是下雪的天氣,也會象征性地多收一到兩文錢。
車夫向車行租車,每日需要向其支付相應的費用。但車行也同樣要受到官府相應部門的管轄,決不能向車夫漫天要價。
如果車行被人舉報有欺負壓榨車夫的行為,查清舉報屬實之後,不僅車行會受到相應的處罰,而且還要暫停營業,進行整改。
不僅如此,車夫如果在載客的時候不按照規定收錢,也會有相應的處罰。只不過比起車行,處罰的力度要小一點而已。
可以說是非常嚴格且完善的制度了。
洋洋灑灑的兩張告示,一條一句簡單直白,還透露着幾分現代制度的影子,一看就是出自謝虞琛之手。
至于謝虞琛寫的規範條例是怎麽變成官府文書,被張貼在城中各處的?可能就需要問問某位在皇宮坐鎮的人了。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嚴格的規定,短時間內在城中興起的人力車,才沒有因為缺乏規範和引導陷入混亂和惡性競争中,進而成為如昙花一現般,短暫興盛又很快凋零的産物。
條例出臺的幾天後,轎夫們向其他人一打聽上面的內容,心中的絕望更甚——
人家這麽嚴格的規範,如此明了的管理,他們這些小蝼蟻如何和那些街上嶄新漂亮的人力車競争。
原本還能憑借擡轎的活計養活一家老小,現在除了那些老古板,誰出門還會選擇乘坐轎子啊?早就讓街邊路旁的人力車夫拉着他們走了好吧?
但唏噓悲傷之餘,在旁人的提醒下:“你們雖然是擡不成轎子了,但是又沒人規定你們不能也跟人家一起,去拉人力車啊!”,很快他們就意識到了這至關重要的一點。
山重水複疑無路,衆人心中豁然開朗,仔細一想,對方說的話确實可行——
首先,既然他們能擡得了轎子,力氣肯定是足夠的。下盤也穩當。不然若是在腳下不穩,一個趔趄把轎子裏的郎君娘子們給摔了或者磕碰了,他們這一行也算是做到頭了。
其次,比起第一次接觸這一行業,拉人力車的那些個“新手”小夥子們,他們還有一點優勢,那就是他們擡了好幾年的轎子,比對方更加清楚城裏的道路。
誰能比他們更清楚京城裏哪條道路最平坦?哪條街巷挑着擔子的貨郎能過得去,但是馬車不行;哪條道上最容易出現當街縱馬的劣跡衙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