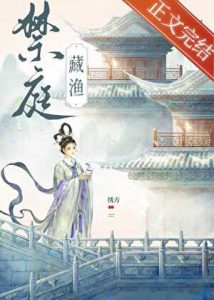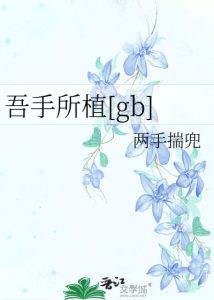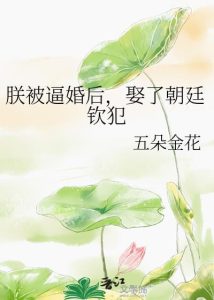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80 章
知道了這件事後, 許大郎說什麽都要專門把食肆的調味品給謝虞琛運過來。
謝虞琛勸了他兩回,不僅沒讓許大郎打消了這個念頭,反而讓他愈發殷切。
最開始只是計劃送各種醬料和不易腐壞的食物過來, 在謝虞琛信中提了一句讓他不必送, 左右也沒什麽會做食肆菜式的人後, 許大郎便計劃連調料帶廚師一并給他送過來。
最後謝虞琛生怕自己再拒絕,許家食肆就要在榆林開分店了, 便只好由着許大郎忙活。
許家食肆現在生意的規模鋪得不小。不僅有食客來店裏消費的收入, 最近還開發出一個“傳授廚藝”的新業務。
與傳統學徒制“三年學徒,兩年效力”的規矩不同,許家食肆搞得有點類似于後世的培訓機構。有意願到食肆進修或是學習廚藝的人,只要向許家食肆交一筆學費,便可以在食肆學習。
雙方自願平等, 沒有什麽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規矩。
培訓班一出來, 便有不少人主動前來報名, 十幾個名額沒過半日便被報滿了。
這種培訓模式人們也是第一回見, 城中的那些酒樓食鋪雖然有心想到這培訓班學習一兩個月,但難免心裏沒底, 想要再觀望一陣,因此第一屆學生基本都是蓬柳村自家的年輕郎君。
這些人會毫不猶豫地報名,一來是因為許大郎的口碑有保證。許家食肆開業後這兩年,從沒有什麽負面消息傳出。食客也都是來了一次後就想來第二次。這些大家夥都是看在眼裏的。
許大郎夫妻二人也都是很和善的性子。有了賺錢的法子從來不會瞞着鄉親們,因此村人們也比較信任許大郎。況且大家都是一個村的人, 擡頭不見低頭見的,許大郎若是真敢欺騙村人, 自己也讨不了什麽好。
而這第二個原因嘛,自然是因為這兩年大家跟着許大郎, 又是養豬又是腌菜的,也賺了不少銀錢。家裏青壯多的,去那些用水泥翻新屋舍富貴人家做工,也能有一筆收入。
手頭寬裕了,自讓願意花些錢財去學一門手藝。
況且他們村又緊挨着官道,除了來來往往的商販,這幾年來他們村做生意的商隊也有不少。
有了這門手藝,農閑的時候在路邊擺個小攤,為那些商販提供些物美價廉的可口飯食,不比去城裏做工的強?
而許大郎也沒有辜負他們的信任,對來學習廚藝的人們從不藏私,盡心盡力地教他們如何做好一道菜。
靠着前幾批學生的口碑,很快便吸引來了從各地專門趕來學習廚藝的學生。
謝虞琛留下新菜式的數量到底有限,食肆不可能一直靠新菜來吸引顧客。再加上不少酒樓都研制出了味道相似的菜品,除了那些吃慣了許家食肆的老顧客,很少有人會願意為了一頓飯專門跑來蓬柳村。
現在許家食肆在市場上的競争力遠不比剛開業的時候。但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許大郎又推出了所謂的廚師培訓課程。
不管是煎炸炖煮、紅案白案,還是許家食肆至今沒有酒樓研究明白的招牌菜式,只要你報名了相關課程,都能在許大郎這兒學到對應的技術。
這套操作下來,食肆的收入反而比原來還增添了不少。以許大郎現在的收入,勻出一點錢來專門雇人定期往榆林給謝虞琛送些新鮮吃食,并沒有多難。
而且有了這定期往來于榆林和江安府的一隊人馬後,許多事情也便利了不少。
譬如這個廚師培訓課程,放眼整個南诏都是第一次見。雖然謝虞琛已經給了許大郎一套完整詳盡的方案。但實際操作起來,還是難免會遇上在計劃之外的事情,許大郎免不了要傳消息給謝虞琛,讓他決斷。
偏這年代寄信又是個極為麻煩的事,不管是托熟識的人捎信,還是花錢請販貨的商賈代為傳達,都有不小的風險。而且也并不是正好就能遇上順路的。
現在有了自己雇的商隊,別的不說,起碼通信來往就比以前方便不少。若是能順路販點別的東西,賺得的錢也能勉強回本。運氣好時,還能稍微賺幾枚銅板。
餘娘子思念小弟時,也能寄一封信到榆林,問問餘小郎的近況。
說到寫信,這段時間餘小郎跟在謝虞琛身邊,別的不說,字可是沒少認。現在他已經基本能看懂餘娘子托人代筆寫給自己的書信了。
至于回信,在先生的幫助指點下,也能勉勉強強湊出百十個字,看起來也是像模像樣的。
作為餘小郎正兒八經拜過師的先生,謝虞琛在餘小郎的教育上也是費了不小的辛苦。
除了最基礎的讀書識字,謝虞琛還專門空出一部分的時間來,帶餘小郎去實際體驗生活,多看多聽外面的世界,與各種各樣的人和事打交道,長長見識。
過去餘小郎一直生活在那個村子裏,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去村裏三裏外的山上砍柴或是摘些榛果板栗補貼家用。
如果說因為阿姊嫁給許大郎,自己跟着到了許家算是餘小郎的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那麽他跟着謝郎離開江安府來到榆林,應該就算是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也真正學到了一些有用的本事。
收到謝虞琛的信時,餘娘子其實是有些猶豫的。一方面,他知道小弟能跟在謝郎身邊,絕對是多少人求都求不來機遇。但另一方面,餘小郎到底是她唯一的親人,年紀又小。
這還是姐弟二人第一次分開這麽長的時間,餘娘子實在有些思念小弟。
但餘娘子心裏也清楚,若真是因為自己這一點不舍之情,讓餘小郎回到蓬柳村,才真是害了他,把他大好的前程給耽誤了。
試想一下,若是回了蓬柳村,他能接觸到的就只有村裏的家長裏短,和地裏的幾畝作物。
自己和許大郎已經算是村裏日子過得最好的了,但眼界也只夠看到前院的生意和後院的醬缸。但跟在謝郎身邊,即使不奢想謝郎的提攜,能學到的東西又何止那些待人接物、察言觀色的本領。
那些在外面長得見識、學到的為人處世的道理,才是最珍貴的寶物。
直到最後,餘娘子也沒有跟任何人提一句讓餘小郎回來的話,只是挑着燈熬了幾個大夜,才趕制出了幾件衣裳和鞋子。
衣服的針腳又細又密,布料也是最上乘的,大小兩套尺寸,托人捎到了榆林。
***
這回前往東山州,謝虞琛計劃還是走水路。
馬匹的速度不慢,卻在舒适性上差了不少。而馬車雖然不用在馬背上颠簸,但這年頭的基礎設施跟不上,官道其實也沒有多平坦。若是遇上大山阻隔,走陸路說不定多要繞一倍的路。
相比起而陸路,水路行船則可以日夜兼程地前行,也不用考慮人和馬匹晚上的休息問題。唯一的缺點大概是謝虞琛自己不争氣,有暈船的毛病。所以要在路上辛苦一些。
臨行前的幾天,謝虞琛把作坊的事都安頓了一番,順便趁着這個機會,把原本的合同也拎出來重新修改完善了。
在作坊,除了作坊的幾個大管事以外,工作量最多的大概就是田福。
最開始他建這個香水作坊的時候,因為手頭的銀錢不夠,所以選擇了與人合夥。作坊經營需要的銀錢,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出自自己的腰包,另外三分之二則分別來自田福和沈家。
不過相比起田福這種斟酌利弊、思慮良久才決定入股的普通生意人,沈家會投資這點規模大小的生意,則更多是為了送謝虞琛一個人情。
至于後來香水在貴族階級內部大受歡迎,成了最緊俏的物品。謝虞琛賺得盆滿缽滿,連帶着命人送到沈家手裏的分紅,數額也大到連飽經世故的沈家家主都忍不住咋舌。這就完全不在沈家預料的範圍之內了。
相較于投了一大筆錢卻像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的沈家,謝虞琛的第二大投資人田福,在作坊的經營上就深入得多。
他不僅包攬了前期所有的原料收購,後續作坊的每一道進展,建廠、招攬工匠、與商販簽訂單、乃至作坊中學堂的籌備,都少不了田福的身影。
換句話來說,田福在謝虞琛這項生意的參與的程度之深,已經不像是個合夥人,更像是他謝家的大管家似的。
雖然作坊也有田福三分之一的投資,但他這段時間的操持謝虞琛也是看在眼裏的。許多事他做了也沒有收益,但只要是他能上心的事,田福基本都不遺餘力地去做了。
謝虞琛便想着趁這個機會,把合同跟田福在原有的基礎上再補充一番,一來是不能讓人家白幹這麽多天,二來也清晰一下職責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