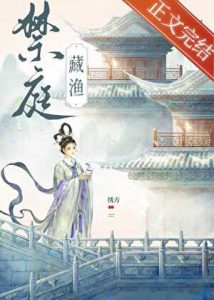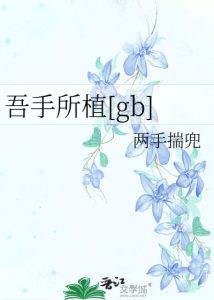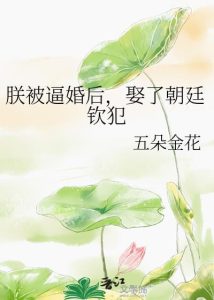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95 章
沈元化對于自己父親的要求倒是沒有多抗拒, 左右他對于謝虞琛這個人是極為喜愛的。
不僅是因為謝虞琛經常能拿出一些人們聞所未聞的新鮮物件,沈元化有時候自己都想不明白是為什麽。可能有些人就是有一種獨特的、讓人忍不住想要交識的魅力。
唯一讓沈元化不滿的,就是他好不容易一路辛勞地從東山州趕回家, 結果沒過幾天, 父親竟然又要他再去一趟東山州。
“就不能托人捎個消息給我, 我就在東山州待着了,還讓我多跑了兩趟。”沈元化同小厮抱怨道。況且從東山州到淮陵的路也不是那麽好走的。
前幾月同謝郎一同去東山州的時候還能走水路, 但現在這個時節賀平鎮那一段的水流, 湍急得別說是行船了,就是那些大牲口想靠近喝口水,都得掂量一下會不會被水流卷走。
現在他想去東山州,要麽就是繞一段路,過了賀平鎮在乘船東行, 要麽就只能乖乖地走陸路。
想起東山州那段颠簸崎岖的山路, 沈元化由衷地深深嘆了口氣, “也不知道我阿耶是怎麽想的, 偏偏選在這個時候。”
“……算了,阿文, 幫你家郎君我收拾行李吧。”沈元化一臉生無可戀地倒在貴妃榻邊的軟枕上。
一旁被叫做“阿文”的小厮趕緊應了一聲,招手從屏風外叫來兩個人,到沈元化的院子裏收拾行囊去了。
沈父不是沒跟沈元化推心置腹地分析過利弊,奈何沈元化天生就缺了那根弦,也沒有他爹那般敏銳的危機意識。在他看來, 他喜歡沈郎這個人,就坦坦蕩蕩地跟人家做朋友就是了, 沒有那麽多彎彎繞繞。
“算了,反正我也搞不明白阿父是怎麽想的, 照做就是了。”沈元化靠在貴妃榻上,理直氣壯地想道。
謝郎那邊生産出來的杜仲膠需要賣到別的地方,剛好沈家有錢有門路。如果謝郎願意的話……應該也算是兩全其美的事吧。
對于沈元化心裏的想法,謝虞琛難得地與他保持了一致。
沈元化這個人的心思很簡單,沒有那麽多複雜的彎彎繞繞,沈家家主雖然是個老謀深算,走一步看三步的人,但為人大致算得上坦蕩。
現在沈家急切地想要和他合作,自己也看重沈家的名望和人脈,和那些不清楚來路的人相比,沈家算是個不錯的合作夥伴,起碼謝虞琛能保證他和沈家之間不會互坑。
至于沈父在信中的內容,姿态算是擺得比較低的,沒有拿自己所謂的“義父”的身份說事,而是把謝虞琛擺在了一個和自己相同的高度,和他商量合作的具體意向。
以沈父的身份,面對謝虞琛這麽一個晚輩,擺出這樣的态度,也算是前所未有了。
沈元化到達東山州的速度算不上快,在他之前,早有嗅覺靈敏的商人聞到的商機。只是謝虞琛這個人平日裏神龍不見首尾的,普通人找不到門路,有的甚至尋到了關泰初那邊。
這些人中,大部分還是想要直接賣杜仲膠的鞋底,一來方便運輸,二來成本也低,那些世家郎君娘子買回去後,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做什麽顏色、款式的靴子。
制作成品的靴子謝虞琛現在已經不奢望了,前些日子建成的那個作坊就是最好的證據。
一個單個的作坊生産力實在有限,光是烏菏一個人的訂單,作坊裏的繡娘工匠們就累了個夠嗆。若是全部由自家的作坊生産,排隊的顧客怕是得等到天荒地老。
這個作坊就只選擇性地接一部分主動找上門的單子。賺得錢足夠維持作坊運轉就行,謝虞琛基本不留着,利潤都留給了作坊裏的繡娘們。相當于他提供一個工作的地點和原料給裏面工作的繡娘而已。
現在整個南诏,就只有他這兒能生産杜仲膠。放眼全國,都是獨一份的生意。但單東山州一州的生産力,實在是沒辦法滿足市面上的需求。直接售賣杜仲膠底實屬沒有辦法的選擇。
雖然如此,但謝虞琛自己是不太願意這麽做的,他還是希望能給東山州當地的百姓創造更多的賺錢機會。
東山州的偏僻貧瘠在全國都是出了名的,百姓賺錢的門路少得可憐,好不容易有了一個杜仲林場,謝虞琛想着盡可能多地讓林場為東山州創造些價值。
只是這個價值還不太好創造,若是制造成品靴子,生産量跟不上,而且也不是随便誰都有這門手藝。但只賣膠底,又不符合謝虞琛的要求。
思來想去,最後還是讓他給想到了辦法。制作靴子比較困難,但做一個鞋底還是很簡單的。
謝虞琛之前在鄉下拍戲的時候,見過村裏比較年長一點的阿嬷制作鞋底,看起來并不需要多複雜的步驟。
老人家生性比較節儉,用的布料都是平常搜集起來的一些零碎的布頭。先把布料拼接起來,再在鞋底外圍用錐子釘一圈孔,最後用一根長針把碎布料縫在鞋底上面。基本就大功告成了。若是手藝精細一點,還會在外面包個花邊什麽的。
阿嬷們還會把鞋面和鞋底進行最終的縫合,但這就不是他們需要在意的了。
謝虞琛想着,完整的鞋子做起來比較麻煩,但這個鞋底還是比較好做的。需要的工具簡單,也不費時。手藝娴熟一點的,一天就能做出好幾雙鞋底來。還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縫制不同的毛皮和布料。
而且只制作鞋底的話,也不需要專門的作坊。人們從謝虞琛這兒領了膠底,帶回家就能做,做完之後再拿到謝虞琛這兒結賬就行。
最開始,謝虞琛規定能做這份活計的必須是現在在林場做工的工匠們的家眷。倒不是有什麽其他的原因,主要是這份活計不需要任何的成本,若是有人領了膠底後,自己帶着東西昧了去,他拿這些人也沒有任何辦法。一對膠底值不少錢呢。
不過這個倒是謝虞琛多慮了,能有一個賺錢的路子,大家夥都很珍惜。
而且在現在這個年代,可能是因為幾代人都生活在同一個地方,民風還是比較淳樸的。即使是比較貧窮的地方,小偷小摸的事情也很少發生。
所以沒過多長時間,謝虞琛就放開了這項規定。只要手藝過了管事的眼,再有兩個同村的人作保,大家就都能賺這份錢。
告示一貼出來,立馬就有幾個婦人跟管事報了名,領了兩雙膠底回去。
東山州下屬各個村縣貼告示的地方,現在都成了人們最關心的地方了。每天有事沒事都要過去看一眼,生怕自己錯過了什麽賺錢的路子。
前些天這個活計還只有林場工匠的家屬能做的時候,可把同村的其它婦人們眼饞壞了,紛紛抱怨自家丈夫當初不能出息一點,被林場選人的管事選了去。要不然她們現在也能靠納鞋底賺錢了。
別的不說,她們鄉下人家的婦人做這些可是手到擒來。一家老小的衣帽鞋襪,哪個不是出自自己的手。若是笨一點手上活計不好的媳婦,在村裏可是要受到別人恥笑的。
盼星星盼月亮的,衆人好不容易盼來了這張告示,林場送到各個管事手裏的膠底當天下午便被他們領了去。
饒是如此,還有許多人來晚了沒領到膠底,最後只好垂頭喪氣的離開,走之前不忘央告管事明天一定要給她們留幾雙。
做這個鞋底首先要有個紮孔的長針。謝虞琛當初在村子裏看到的阿嬷們都是用一根鐵錐,但在這個年代鐵制品還是很昂貴的,鐵錐大家怕是用不起了。
不過這可難不倒大家夥。有人從山裏砍了一種材質很硬的老竹子,削尖了做成竹錐,紮起孔來也很是順手。還有人用牛骨在石頭上磨成了骨針……
形形色色的方法各有千秋,就連謝虞琛聽說之後,都不由地感嘆了一句人民群衆的智慧還真是偉大。
除了杜仲膠底,謝虞琛這段時間又琢磨起了輪胎的制作。只不過比起鞋底,輪胎的難度明顯大了幾個量級。謝虞琛找了好幾個木匠,按照他給的圖紙制了模具,但得到的成品都不太理想。
到最後謝虞琛直接放棄了自己制作,讓人放出消息,就說自己現在想要用杜仲膠制作一個能用在馬車上面的車輪,若是有人能提出有價值的意見,賞錢一貫;若是能制出成品,不僅直接賞十貫賞金,而且林場還會聘用他為技術顧問,每月工錢都有半貫。
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謝虞琛給出的這個條件足以算是重賞了。消息放出去後,林場那邊招攬來不少手藝高超的木匠。謝虞琛直接把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小組,專門負責包括輪胎在內的各種模具的開發。
後世空心的輪胎以現在堪稱簡陋的技術還生産不出來,謝虞琛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實心的輪胎。但一個車輪光用杜仲膠制作的話成本不免太高。
最後還是幾個工匠想出了一個辦法,大致就是把一個車輪分成三個部分。最外面的自然是一層寸許厚的杜仲膠,刻上各種防滑的花紋,裹在最裏層的硬木上面,中間則用一些比較柔軟的物質作為填充。
謝虞琛聽到這個辦法之後都有些驚訝。這幾個工匠的辦法雖然聽起來簡陋,但卻奇跡般地滿足了一個合格的車輪應該擁有的全部條件——
最裏面的硬木讓車輪有了足夠的支撐力,中間的填充物和外層的杜仲膠既做到了讓馬車減震,又可以讓車輪承受更大的形變。
如果不是見過了後世的車輪胎,連謝虞琛都會認為這個方法是最優項了。
因為幾個匠人都說這個法子是他們衆人一起想出來的,所以謝虞琛很大方地給他們每人都拿了十貫的賞錢。若是他們願意留在作坊,職位就是謝虞琛之前說好的每月半貫錢的“技術顧問”。
若是不願意留下來,謝虞琛也不強求,以這些人的技術,不管去到哪裏都不會愁一口飯吃的。
不過憑心而論,謝虞琛還是希望這些人能留下來。在這個年代,一個優秀的技術人才有多難能可貴,不用說都清楚。更何況謝虞琛的野心還不止如此。
早在幾個月前在榆林的時候,謝虞琛就有過發展科學教育的念頭。後來在香水作坊的那個學堂成功創辦後,更是堅定了他這個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