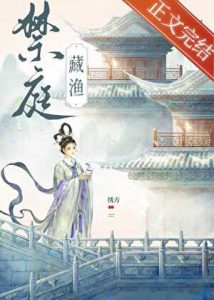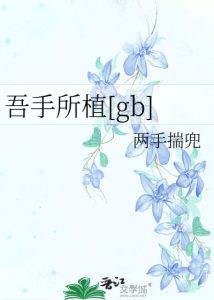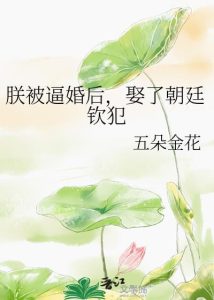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58 章
在其它地方, 冬天一般都是百姓們家中最清閑的時候。
田間地頭都被一層厚厚的雪被覆蓋,山上也是光禿禿的。沒什麽正經活做,人們便把門窗一關, 在屋裏燒起火來。
外面寒風凜冽, 屋裏卻暖乎乎的。爐子裏的木柴噼裏啪啦地響, 一家人擠在屋裏,要麽說說閑話, 要麽就搓搓麻線, 編編竹籃之類,有一搭沒一搭地做着活。
冬天算是百姓們為數不多可以歇息的日子。等到一開春,河裏的冰一化,他們又要扛着鋤頭到地裏忙活,去賺下一年的吃用了。
百姓們往自家一躲, 外面就顯得冷清寂靜起來。就連平日裏最繁華的官道, 入了冬之後, 行人客販也會驟減。街頭巷尾那些叫賣的聲音也比平常少了大半。
從過去到現在, 許多年來皆是如此。
這時候,就顯得蓬柳村格外特別, 成了個與周圍地方都格格不入的“異端”來。
就連跟在烏菏身邊的金甲軍,平日裏見多了大場面的人,第一次踏進蓬柳村的時候都會忍不住感慨一句:“此地當真是特別,一個不起眼的村子,竟比他們一路走來時途徑的許多城裏還熱鬧!”
沒辦法, 畢竟蓬柳村所處的地理位置特別,自打灣水縣到定徐的官道修起來後, 蓬柳村人便靠着這條毗鄰的官道掙了不少錢財。
雖比不上像大漳村那種土壤肥沃的地方富裕,但村人們的日子也絕對算不上艱苦難捱。
而且“交通便利”的好處可遠不止開間客舍或是茶攤食肆, 賺取路來路過的行人銀錢這一點。有了這條官道,蓬柳村的百姓不管做什麽,事情都比別人要容易許多。
就拿村民們這段時間最忙碌的兩件事來說,一個養豬,一個腌酸菜。要不是離得官道近,每天光是經過他們村的行商就不止十個八個,村人們的豬肉和酸菜也沒那麽容易能賣出去。
酸菜倒是不怕放,可豬肉不行啊。冬天還好,一塊豬肉挂在外面一晚,第二天便凍得硬邦邦的,也不擔心會壞。可要是換了天氣最炎熱的七八月,又濕又熱的天氣,像肉啊菜啊之類的東西,最是容易腐敗變質。
要不是蓬柳村緊挨着官道,道路平坦,運輸東西的速度也快。再加上離灣水縣也只大約一個時辰的距離。村人們哪有機會在自己家中殺了豬後再把豬肉運到城裏。
自然也沒了那些豬血、豬內髒,供他們制成熟食賣出去或是留着自己吃。
畢竟灣水縣富庶,那裏的百姓舍得吃,拉到集市上的豬肉便也不愁賣。
現在蓬柳村的百姓不僅平日裏有莊稼要侍弄,家裏還都或多或少養了幾頭小豬,一頭豬算下來賺得也不少。更別提冬天還能腌酸菜。平日裏靠着租借家裏的空屋舍,一天也能有幾文錢的收入。
若是這些還不夠他們忙活,像王家兄弟這種人口興旺的人家,爺娘叔伯和幾個年長的忙活田裏的事情,家裏的豬有下面幾個小的照看。家裏的其他人便會到許家食肆去做工。
幾個半人高的娃娃,倒是把煮豬食、清掃豬圈、喂豬、割草等許多活計分得清清楚楚。家裏的幾頭豬也被他們照料的圓滾滾胖乎乎,身上的豬膘肥得發顫,誰見了都歡喜。
王家大郎和二郎便是“出去給人做工”的那個。今年開春的時候那石灰砂漿火了,便是他兄弟二人帶着村裏的小夥子們,給那些富庶人家刷牆抹灰。
後來石灰砂漿的生意漸漸飽和,又到了冬天,天氣寒冷不便興修土木。王家兄弟二人便回家把後院的大缸給搬了出來,為今年入冬後的腌酸菜做準備。
之前王家兄弟二人的親娘,也就是王家大嫂,她便是在食肆做工,為人處世都很得食肆衆人喜歡。
之後又因着給許大郎說了那門和餘娘子的親事後,跟許家的關系愈加親近。許大郎便破例讓王家大嫂帶着食肆的菜譜回了家。
要知道許家食肆的菜譜在外面可是金貴東西,許多食肆酒樓都開了高價地要買。
而且打前些日子許大郎按照謝虞琛的吩咐,在食肆裏開辟了什麽餐飲教學的業務,招收學徒學習廚藝後,食肆食譜的價格就更是往上翻了一番。
現在能在許家食肆做工的人,要麽就是拿了賣身契的奴仆,要麽就是簽訂了保密的協議。
像王家大嫂這種能拿到食肆方子的人是少之又少。基本只有最開始雇傭的那一批幫工,又一直留在食肆裏盡心盡力地做事,手裏才能攢下幾個食肆淘汰下去的菜式食譜。
不過即使是許家食肆淘汰掉的食譜,放在其它地方也是很招人稀罕的。
就拿之前陳家送到食肆的仆役來說,和許大郎約定的期限到了之後,他們便帶着五香豆幹、銀絲酥一類吃食的制法回了定徐縣,開始在陳家的鋪子裏做工。
後來許家食肆因為忙不過來,便停止了那些外賣吃食的生産。可人們沒吃夠怎麽辦?別人家又做不出那個味道,那這生意不就全部落在了陳家人手裏。
光靠着像豆幹、瓦罐雞一類的吃食,陳家的那幾個鋪子這一年就沒少賺錢。王家大嫂從許家食肆那兒學到了幾個菜式也是同樣的道理。
雖然新鮮勁過去,食客們對于這些吃食不像是剛推出的時候熱切。但那些菜品的味道還是很好的。長些時日不吃,心裏還有些想念惦記。
王家大嫂帶着菜譜回去後,便與家裏人商量,自己從食肆裏學了那麽些厲害的庖廚本領,許大郎又是難得的寬厚,允許自己在外面做這幾道菜,那他們何不自己也開一間小食肆?
至于食肆的位置,就開在官道旁,菜色也不必像許家食肆那樣精巧別致,只賣些尋常的酒菜,以價格實惠,便宜大碗為主。
王家大郎和二郎是在外面闖蕩,見過世面的人,腦子轉得也最快,聽完自家阿娘說的話,便覺得确實有幾分道理。
官道上每天來來往往,趕路的百姓和挑着擔子的貨郎那麽多,總是要吃飯的吧?他們賣些物美價廉的吃食,雖賺不了大錢,但也絕對不會虧本。
眼看着最精明的大郎和二郎都同意了這個計劃,家中其他人自然也不打算阻攔。只是要開食肆的話,就算只是在官道邊上支個棚子,那也是要不少花銷的。
他們王家雖然平日裏不缺衣少食,日子也算過得去,但掏出一筆開店的銀子,對他們來說也是有些難度。
這段時間王家人都拼了命地幹活,腌酸菜、養豬、在許家做工,比農事最繁重的時候還要忙碌,就是想着能在開春的時候攢下一筆開店的錢。
既然是開店,那就免不了和經商打上交道。這個年頭還有戶籍這道門檻,農戶是不能随便經商的。
王家人好好的農籍,官府分給他們百十畝田地,其中還有不少永業田,是能繼承給子孫後代的。怎麽可能為了一間食肆把祖宗家業、立身的根本給丢了。
不過這到也是個複雜事情,他們雖沒有經驗,但許家有啊。看許大郎食肆的生意那麽熱鬧,也沒見他因為這個丢了山上的土地。
但王大郎的二叔又說,別忘了許家食肆除了有許家之外,還有一個謝姓郎君。許大郎能保住自己農籍的身份,保不齊是因為有謝郎在背後支持。
衆人一想,也覺得有道理,便還是打算親自問問村裏正。
和蓬柳村的裏正一樣,每個百戶以上的村落裏都有正副兩位裏正。主要是負責戶口和納稅一類的事情。村裏人若是有了什麽矛盾,如果不能在私底下解決,也是會由裏正來處理。
不過嚴格意義上來說,裏正也不是什麽特別重要的政府官員,所以一般都是由在本村比較有聲望的長輩來擔任。平日裏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樣種田砍柴。
像是許家食肆這種情況,在這個時代還是比較少見的。饒是蓬柳村的裏正見多識廣,也沒遇上類似的情況。
普通百姓農閑的時候去山裏采點菌子山貨拿到城裏賣掉,是再正常不過的吧?家裏有幾間空屋子,打掃出來給過往的行商居住,收取一點住宿費,也不能因此就說他們是商戶吧?
許家食肆的生意本質上和這些也沒什麽太大的差別。畢竟許大郎沒有離開自己的土地,每季度也沒有脫離過農業生産。就連開辦食肆的地方,都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只是規模做得大了些,但也勉強能算作是符合規定。
再加上許大郎背後的謝虞琛身份又神秘,村裏正也不想得罪對方。而且自家廚房的角落裏,還端端立着兩個酸菜大缸呢。因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便也由着對方去了
像許大郎這樣的行為,放在其他地方,同村的人肯定會有意見,但偏偏到了許大郎這裏,村裏人便如什麽都沒看見似的,默許了這一現象發生。
村人們能容納許大郎,一來确實像村裏正說的那樣,許家的行為在律法上并沒有明确禁止,屬于只要不深究就能說得過去的那種。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許家食肆的存在并沒有損害村人的利益,反而給他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帶動了整個村子的經濟發展。
百姓們因着許家的存在,多了不少賺錢的門路,感激還來不及,又怎麽會去主動找許家的麻煩。
而且許家的地也确實貧瘠了點,屬于主動給別人,人家都可能因為一年到頭的收成與付出不成正比而拒絕的那種。實在是沒有必要為了這樣貧瘠的地跟許家對上。
當初因為許家人丁不豐受人欺負,才分到坡上的土地,雖然有更大的宅基地作為補償,可只要是有腦子的,誰不知道這兩者完全沒法比。
只要是個平坦開闊的地方,随便平整一番,便能用來建造宅院。若是不嫌偏遠的,找塊荒地亦可作宅基地。
可那禾苗是哪裏都能種的嗎?首先光是土壤不豐厚這一項,就排除掉了大半的土地,更別說禾苗種下去後還需要灌溉澆水。
大幾十上百畝的土地,離得水源遠一尺,他們就要多一番辛苦。
能有一塊土壤肥沃、位置還好的土地,那是多少人家夢寐以求的東西,哪裏是一塊宅基地能比的?
本來村人們就因為當初分地一事上,對許家有所虧欠。現在許大郎過上了好日子,連帶着他們心裏頭也舒坦了些。
在數年前虧欠了許大郎一家不說,之後沾了許大郎的光,靠着養豬腌酸菜賺了好些銀錢後,還不懂得知恩圖報,反而要倒打一耙,掰扯什麽農籍商籍的事情,害人家連土地都丢掉。
要是他們蓬柳村的人真做出這種事情來,那真是沒臉見人了。別的地方人知道了,也得戳着他們蓬柳村人的脊梁骨罵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