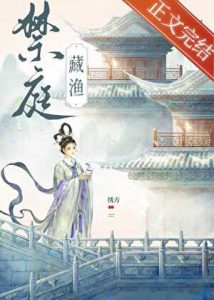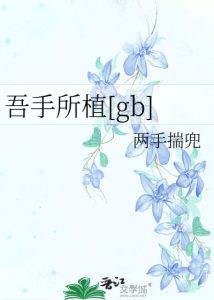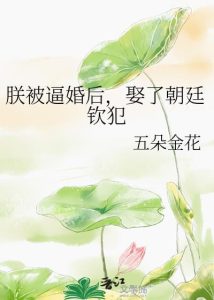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62 章
蓬柳村自劉家敗落後, 客舍生意就又紅火起來。再加上來許家食肆吃飯的食客大多不是從城裏來的郎君,拖家帶口或是約上三五好友,就是為着和謝虞琛的生意而來的貨郎。這些人基本都會在蓬柳村住上幾晚。
許大郎夫妻兩個就商量着, 把院子裏空着的那一排屋舍都拾掇出來, 請人打了家具做成客舍, 租住給食肆的食客們。
沒想到客舍剛收拾好,迎來的第一批住客便是那些金甲衛的士兵們。
到最後食肆的食客還是要去村裏別家去住。別的不說, 要想來食肆吃頓飯, 每天還得多走幾步路。
不過即使麻煩,人們也都是願意多走幾步路來許家食肆的。沒辦法,誰讓食肆的飯菜就是比別家的美味呢。
除了在許家食肆,別的地方的酒食就是再貴,也抵不上食肆的什麽紅燒肉、烤鴨、手撕雞, 勾得人食指大動, 光是聞着味就胃口大開。
這些別的地方都做不出來的菜色, 才是許家食肆硬氣的本錢。
當初擴建院子的時候, 謝虞琛就特意多規劃了兩排屋舍。當時許多人還咋舌過許家的大手筆。
那時候許家還沒有食肆的生意,許大郎手頭也不像現在寬裕。能掏出那麽大一筆錢來修葺屋舍, 也是很下了一番決心的。
這麽一看,從做麥芽糖開始,買稻米、建屋舍、開食肆,再到半月前大肆收購幹花,每次都幾乎是一場豪賭, 把手頭全部的籌碼都投入到下一場生意中去。
光是許大郎一人自然是沒有那麽大的魄力。他也知道自己才幹有限,因此這些決定幾乎都是謝虞琛替他做的。而後才有了許大郎的今天。
若不是謝郎, 他怕不是還守着自己山坡坡上的幾十畝地,饑一頓飽一頓地熬日子。雖說他能進山摘山貨貼補生計, 可他還有當初建客舍時欠的錢需要還。
山裏又多是豺狼毒蟲,指不定哪天不小心踩空跌倒山崖下面,就落得個和錢家二郎一樣摔斷腿的結局。
可以說沒有謝虞琛就沒有許大郎今天的一切,許大郎也明白這個道理。謝虞琛之前和他提的那個在改種樹木的建議,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許大郎都應該答應的。
況且按照之前的經歷看,謝虞琛做的決定就從來沒有出錯過。許大郎前段時間會糾結不定,純粹是因為土地對于當世的人來說,實在是太過重要。
不過他也只猶豫了幾天,便決定把那些地都交由謝虞琛處置。最開始做下這個決定的時候,餘娘子還有些猶豫,張嘴想勸勸自家夫君。
她對謝虞琛敬畏雖不比許大郎少,但畢竟沒跟着他們親身經歷食肆起步的那段時間。聽到許大郎說,謝郎似乎是想把後山的那些土地都拿去種樹後,她便有點遲疑。
再怎麽貧瘠也是土地啊,是能結出糧食的。種了樹可就什麽都沒有了。
雖然食肆的生意足夠紅火,又有醬油、酸菜等旁的收入,生活也足夠富足。但土地就像是一個兜底的東西。有了地,人們的心裏就是踏實的。
這大概是一種“即使生意做不下去,他們還有土地,可以種糧食,在這年頭就餓不死”的想法。
若是沒了這個兜底的,即使他們現在吃穿不愁,餘娘子也總覺得心裏空落落的,踏實不下來。
但最後,餘娘子還是同意了自己夫君的話,把耕田改種樹木。原因也無他,是那天夜裏許大郎和她說了之前的日子,按着謝郎指揮,是如何從一窮二白到有了現如今的産業。
當初不明白許大郎為何要把院子修得那麽大的村人,現在不也都在背後議論,說許家有遠見。現在蓬柳村人來人往如此熱鬧,蓋再多的屋舍,也不愁租出去。
而且眼看着食肆的生意越做越大,就連客堂都在前月又擴大了兩間。這段時間廚房那邊庖廚們也嚷嚷着廚房不夠用,炒菜的時候連身子都快轉不開,催促着掌櫃也就是許大郎再騰一間廚房出來。
若不是當初就把院子修得如此完善,現在他們指不定要為了屋舍不夠用怎麽發愁呢。
許大郎還告訴妻子,說自己前些日子去肥皂作坊那邊給那裏的金甲衛送飯,和其中幾人随便聊了幾句。
那幾個金甲衛便在閑聊時告訴自己,他們此行是護送謝郎從羅西府回來。但啓程的幾個月前,北邊的東山州發生了水患。
為了安頓災民,當地的官員便按着他們大人的建議,開辟了一大片的林地種杜仲樹。
杜仲樹原本是秦嶺一帶的植物,樹皮可以入藥。但這回在東山州栽種杜仲樹林,似乎并不是為了賣給那些藥鋪子。謝郎說起杜仲樹林的時候,也提起像什麽經濟作物一類的詞彙。
有了這些話,餘娘子心裏便踏實了不少,沒再繼續勸自家夫君。許大郎便挑了個合适的時機和謝虞琛說明白了自己的意思,把自己拿幾十畝土地都交給了對方規劃。
對于杜仲樹林,金甲衛在許大郎面前的說辭是烏菏命當地官員開辟。但他們心裏都清楚,那其實是謝郎頂了他們大人的身份做的。
他們大人那時正喬裝打扮前往綏桐,探查私鹽一案。真正帶着人赈災、開辟荒林的其實是謝虞琛。
但這些話是萬萬不能說出口的。幾個金甲衛士兵也只好含糊地提了一嘴,說他們大人之所以能想出開辟杜仲樹林,還有什麽水泥作坊的辦法,其實都是因為聽了謝郎的建議。
雖然不能真正意義上地為謝虞琛正名,讓他的功績為百姓所知。說這些都是受了謝虞琛的建議,也算是在目前條件下,他們能為對方做的最大限度了。
金甲軍作為受烏菏直接領導的軍士,許多時候他們的一言一行,其實就代表着烏菏的想法。在東山州赈災一事上,烏菏對于謝虞琛,心裏其實是有些虧欠的。
治理東山州水患和發明水泥,光這兩樣的功績,就足夠在一衆朝臣中脫穎而出。更別提等到杜仲樹林開始産膠的時候,又會對經濟和百姓的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
若是把這些政績算在謝虞琛頭上,別說是一州刺史,憑借着閃閃發光的履歷,就算是更高一點的位置,有烏菏扶一把,謝虞琛也是做得的。
但是因為要隐瞞烏菏查案的行蹤,謝虞琛扮做對方的模樣,他對于東山州百姓的貢獻,也都只能算在烏菏的名下。
更重要的是,謝虞琛明知他在東山州做的一切,雖算不上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但對自己的好處也是寥寥無幾。可為了當地的百姓,他還是盡心盡力地做了那些事。
整改仲學文手底下的那些私人采石場,為百姓鏟除仲家這個地頭蛇;組織當地官員抗洪救災;開辦水泥廠、杜仲林。以工代赈,安置受災百姓。
……
一樁樁一件件,都是對民生大有裨益的好事,謝虞琛卻從中沾不上半點好處。
頂着烏菏的身份,不管到哪都有當地官員殷勤熱切的招待,他只需享受着玉盤珍馐、百官奉迎,完全不必費不眠不休奔波勞累的辛苦,做那些吃力還不一定讨好的事。
但謝虞琛卻還是做了,沒有絲毫怨言。烏菏盡可能地補償對方,像是寄信給淮陵沈氏,答應與對方的合作。只為給謝虞琛撈一個合法且顯赫的身份,便于他日後行事。
還有其它暗地裏的補償,雖然也有一部分是烏菏自己的私心作祟,但謝虞琛在東山州做的一切,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至于烏菏為什麽會選淮陵沈氏義子的身份,這裏面涉及的原因就要更複雜了。
世家和皇帝的矛盾這幾年幾乎已經擺在了明面上。而新帝年幼,尚不能完全親政,皇帝的想法說白了其實就是烏菏的想法。
世家和皇權,二者的關系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前朝便是由世家把持着朝政大權。到最後就連由哪一位皇子繼位,都變成了他們背後支持的幾個世家争奪決定。
皇帝完全被世家架空,官員選拔升降,也完全由他們的家世的決定。整個朝廷上下,一大半是不學無術卻憑借着世家身份而身居高位、屍位素餐之人。
不僅是選官,世家的勢大還帶來了像土地兼并等諸多問題。百姓無地可耕,只能賣身為奴,許多人口也被世家大戶隐瞞。
國家的財政收入一年比一年少,就只能加重賦稅,如此又導致更多的百姓淪為世家奴隸,世家勢力更加強盛。
世家勢大的結果便是國家對地方失去管控,導致土地兼并愈加嚴重,百姓失去耕地。如此惡性循環,百姓的日子越過越艱難,地方割據,前朝也因此覆滅。
等到南诏建國,一統天下。雖然最開始為了國家安定,對世家主要采取安撫的政策。但每一任皇帝心裏都謹記着前朝覆滅的原因,對于世家大族一直都不曾放松警惕,基本都是以打壓的态度為主。
到了烏菏這一代,皇權逐漸穩固,世家與皇權的矛盾便終于被擺到了明面上。烏菏更是手段強硬,劍鋒直指朝中那些只有家世,并無一點才幹的蠹蟲。
烏菏态度這麽鮮明,那些世家大族也不傻,不可能半點不反抗,任由烏菏的刀劍往自己的脖子上搭。
這幾年明裏暗裏的,烏菏但凡行錯一步,或是有一點疏忽,怕是就性命難保,大大小小的刺殺也受了不少。若不是他身份特殊,以南诏大巫的身份輔佐幼帝,恐怕朝中也難有他的一席之地。
但世家與世家之間,關系也并非通同一氣。許多小的家族,基本都保持着觀望的态度。他們不像那些大世族權勢滔天。雖比起寒門小戶有一些特權,但大多還是遵紀守法。
像是之前搬到蓬柳村的劉開一脈那樣欺壓百姓的也是少數。皇帝打壓世家的巴掌一時半會扇不到他們身上,他們自然沒必要跟着着急。
像是之前陳六郎的阿父教導自家兒孫時說的那樣,對于朝中争鬥,他們敬而遠之,對哪一方都不特別親近,明哲保身才是生存之道。
而牽扯到權勢争奪中的世家高門,烏菏也沒有那麽莽撞,打算一下子和他們所有人對上。用拉攏一半打壓另一半的辦法,将其分而治之才是正确的策略。
畢竟刀沒有真正架到自己脖子上的時候,誰都覺得自己是那個鹬蚌相争中得利的漁翁。
就像之前的私鹽一案,從中獲利的是世家。但把這一案的導火索,也就是那張假的鹽引捅到烏菏面前的,也同樣是世家出身。
畢竟誰都知道鹽業一行利潤巨大,可鹽業也不是誰都能分一杯羹的。
如果把鹽營比作桌上誘人的珍馐美食,那麽那些世家就是在一旁垂涎三尺的食客。
這場私鹽案,便是因為桌上的位置有限,只有把原來分割美食的人拉下去,空出桌上的位置來,那些在遠處望的人才有機會坐到席上,品嘗到桌上的絕世美味。
烏菏想要打壓世家氣焰,世家又何嘗不想借烏菏的勢為自己掃清政敵呢?
一場私鹽案,下獄的官員從綏桐到沛川再到京城,有近百人之多。
如此雷霆手段,清掃一批世家豪強後,空出來的那些官位,一半由在這一案中出了力的世家兒郎擔任,而另一半則是落在了由烏菏選出來的人身上。不論出身,能者任之。
而除了明哲保身的小世家、拉攏一批打壓一批的豪強以外,世家裏還有最特殊的一派,也就是順應趨勢發展的淮陵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