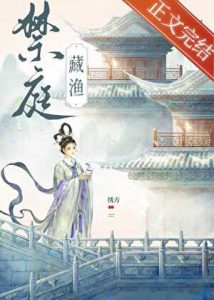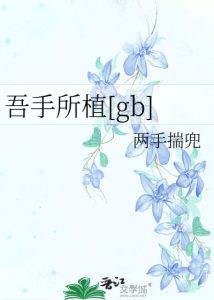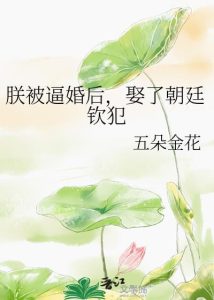其實朱棣早在很久之前,便已經知道了離墨的存在。
李泉賦在那封托他救人的書信中,就已告知了他有關離墨的一切,并承諾,作為保護妹妹的條件,願意将離墨奉上。只是,李泉賦并沒有告訴他,李泉詩,根本就不知道離墨的存在。
那般驚人的財富,對于一個有着不小野心的人來說,誘惑自然是極大的。李泉賦的确是算計得很好,離墨如今下落不明,唯一有所關聯的人卻毫不知情,沒有如願得到離墨的朱棣心中自然是有所不甘和忿恨的,可抛開對李泉詩的感情不說,他也不能将她如何,因為說不準,李泉賦對李泉詩的哪句囑咐與暗示裏,就藏着離墨的下落。
他将這些告訴了徐瑾,也不過是想表示自己之所以對李泉詩如此特別,是事出有因的。卻是未曾想到,李泉詩知道之後會反應如此激烈。
“你要搬出去?”朱棣皺着眉看着李泉詩,後者低着頭,站在案前。
“這段時日多謝王爺厚愛,泉詩思慮多時,終是覺得長住王府于禮不合,泉詩雖則是一介孤女,卻也懂得禮義廉恥,還請王爺應允。”李泉詩說。
“胡鬧。”朱棣有些惱怒,“這燕王府裏,還有人敢怠慢你不曾?”
“自是沒有。”李泉詩說:“是泉詩于心不安罷了。”
“哦?”朱棣氣極反笑,“有何不安?”
“王爺對泉詩諸多恩施與照顧,泉詩卻給不了王爺離墨,實在無顏再繼續待在王府。”李泉詩說得很平靜。
朱棣有些愣住,良久,他說:“你說我是為了離墨?”
李泉詩沒有回話。
朱棣看着她,聲音有些冷:“你先回去,這事之後再提。”
“但求王爺應允。”李泉詩福了福,靜靜退下。
可後來的結果卻是,雖然朱棣并不願意,李泉詩還是搬了出去。
“王爺若是為了離墨,大可不必憂心。李姑娘依然待在北平,身邊帶着的也是王府的人,若她不情願待在王府,強留倒是不美了。“徐瑾溫婉地說。
徐瑾早為李泉詩找好了住處,那日朱棣剛一提起,徐瑾就不緊不慢地将話給堵了回去,朱棣面色冷了冷,終于也是不曾多說什麽了。
而一晃眼,就是三年。
李泉詩在城裏制墨為生,雖然王府每月都會遣人送銀兩與物品過去,可卻從未見她用過,朱棣時不時也會去那家名為“木蘭齋”的小店看看,哪怕李泉詩一直都是冷冷淡淡。
北平人都知道這木蘭齋與燕王府關系不一般,如此之下,李泉詩生意倒也算熱鬧,也未曾遇到什麽麻煩,一千多個日夜,就這麽在悠悠墨香裏過去了。
三年以來,關于李泉賦的事像是被遺忘了一般,李泉詩再沒有主動問過朱棣什麽,而朱棣這一邊,似乎也再沒有了新消息,也唯有午夜夢回時,李泉詩才知道,自己從未忘記那份傷痛與恨意。
那天徐瑾提起擇婿之事,李泉詩心中在驚愣過後也不過是一片平靜,如今的她,早沒有了選擇的權利,她一生的美好與希望,似乎都已埋葬在三年前的冬日,再無複蘇。
而過了夏至,朱棣又一次來到木蘭齋。
“我過幾日要去徽州,你可要同行?”朱棣一開口,李泉詩便僵住了。
徽州……有生之年,竟還能再回去嗎?
“之前總怕你觸景生情,便也沒有提過這事。此次我正好有事,你若願意,便一同去看看吧。”朱棣看着眼前的人,語氣不由輕軟了幾分。
李泉詩咬了咬唇,說道:“那就多謝王爺了。”
當李泉詩再一次跨進李府大門,哪怕身在盛夏,渾身也如處寒冬,那股血腥味像是又再次迎面撲來,李泉詩只覺頭暈目眩,臉色慘白。
“你怎麽了?”朱棣看着李泉詩,不禁擔心地說,“若是不舒服,就別再進去了。我們……”
“無事……”李泉詩深吸一口氣,擠出了一個笑容,“若這次再不好好看看,怕是這一世都不會再回來了吧。”
朱棣臉上神情複雜,可終是沒有再說什麽。
經過一處涼亭時,李泉詩停了下來,她喃喃地說:“兄長以前最愛在這看書,每年夏天荷花開時,我便請幾個閨中好友來府上做客,我們在此賞花,那回兄長落了東西,回來取時正好遇見我們,兄長那日穿得是慣常的白衣,眉目如墨畫般清俊,我記得,所有人只看了一眼,就都羞紅了臉……”
“兄長脾氣溫和,我從未見他對誰紅過臉,對家裏的下人也是。每次被我氣急了,也只是用書敲一敲我的頭,微笑着搖頭。”
“那麽好的一個人,怎麽就會這麽去了呢?”李泉詩像是問朱棣,也像是問自己。
“世事本無常。你兄長之所以明知有難也不離開,就是為了保全你,為了他,你也該好好活下去。”
李泉詩笑了笑,沒有說話。
“我記得我曾說過,我與令兄,也算是至交。李府我也曾來過多次,也……曾見過你多次。”朱棣看着李泉詩,慢慢地說。
李泉詩看着朱棣有些深邃的眼神,不知為何有些慌張,“我……我不知……”
“我知道你不信我。”朱棣的語氣變得極為認真,“可若我說,我對你的确未曾存任何利用之心,我只是單純地想對你好。我雖是燕王,很多事卻身不由己,我原不想委屈你,可是那日徐氏說要為你擇婿,我才知道自己遠沒有想象中那麽灑脫。所以,回北平之後,你可願入府?”
李泉詩有些不知所措,心裏幾種情緒混亂地交錯,她不知該對眼前的人相信幾分,理智告訴她該果斷地拒絕,可是心裏卻總是生出萬般不舍與難過。
“你不用急着答我,這幾日,好好想想。”朱棣說完,向前走去。
朱棣是真的沒有将李泉詩逼得太緊,剩下的幾日在徽州,除了每日的幾句問候,他再不曾與李泉詩多說什麽。李泉詩一個人思來想去,也不知該如何抉擇,雖然心意未決,但到底是有了一些偏頗的了,這一趟徽州之行,讓她覺得三年來的一切更是艱辛和勞累,如果,真的能有一個人陪她一起走下去,或許也是一件好事?
離開徽州那日,馬車行至城外,路途有些熟悉,李泉詩驀然想起三年前自己離家那日,就是從這條路去往城外的寺裏,她心念一動,決定去寺中看看。
這座小寺依然是掩在竹林間,那個須發皆白的主持看見李泉詩,竟也是不驚不訝,他笑了笑,說:“李姑娘到底是回來了,那有些東西,也該物歸原主了。”
朱棣并沒有陪李泉詩上山,李泉詩命随侍在院裏的等候,自己一人跟随主持進了大殿。
“這是?”李泉詩接過錦盒,有些不解。
這個狹長的盒子對李泉詩來說很是熟悉,因為這是李家所特制的用以裝盛好墨的盒子。
“三年前,這是李施主親自交于老衲的,可還記得?”主持的聲音很溫和。
記得,當然記得。李泉詩嘴角勾起一個苦笑,說:“那大師現在為何将其給我?”
“老衲說過,物歸原主。李施主不妨打開看看。”主持笑了笑,說道。
李泉詩愣了愣,随即似是想到了什麽,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抖起來,掀起盒蓋,一方黑墨上,是一紙書信。
李泉詩深吸一口氣,展開了信。
作者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