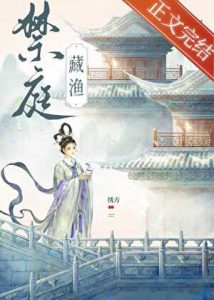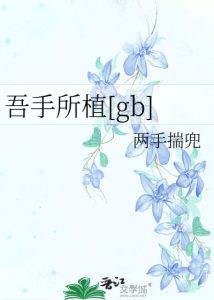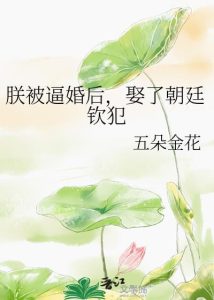定做
眼看着泡菜這麽受歡迎,那些沒趕上趟的人家,心裏多少有些着急,一天不知要往放酸菜缸的屋裏跑幾趟。
要不是還記着謝虞琛的吩咐,讓他們沒事不要打開酸菜壇子,免得讓不幹淨的東西進去,導致酸菜發黴變質。他們怕不是要天天打開蓋子,瞅一眼裏面的泡菜是不是發酵好了。
也不是他們耐不住性子,實在是眼巴巴看其他人家靠着賣酸菜又是換糧食,又是賺銀錢的,他們家的酸菜卻不知道要等到什麽時候才能發酵好,心裏着急啊!
晚一天發酵好,就少賺一天的錢。
萬一等他們的酸菜腌好了,人家又不流行吃這個了,那可怎麽辦?
但他們再着急也沒用,酸菜的發酵總是需要時間的。
酸香會随着時間的積累慢慢變得濃郁,最終散發出酸菜獨有的香氣來。
好不容易等到酸菜腌好,蓬柳村的村人們是一刻都不願意耽誤,挑着擔子就往附近的村子裏趕。
托了最開始賣酸菜的那批人的福,現在他們蓬柳村酸菜的名聲在附近幾個村子裏已經積攢下不少。
人人都知道那醬蘿蔔下飯吃最好,酸白菜煮豆腐炖菜最香。
蓬柳村的村人們只要挑着擔子到村口,說是來賣酸菜的,總不缺人拿着米面出來跟他們換。
若是挑到城裏賣給那些食肆酒樓,還能多賺幾文錢,就是要多走些路程。
王氏兄弟一家是最先學到腌菜手藝的。他們家幾個媳婦做事也麻利,跟着婆婆一起在家裏腌了不少酸菜。
王家男郎則負責買鹽、去醋坊打醋、搬酸菜缸這些費力氣的活兒。
王家本來人口就多,這一忙活起來,人們進進出出的,就顯得十分喧鬧。
熱鬧在他們眼裏是件好事。
熱鬧說明有事做。有事做有活幹,日子就有盼頭。
因此,即使這些天來他們一家老小都少有能閑下來的時候,但大家面上心裏都是歡喜的。
天氣好時,王家兄弟幾人還會把祖母搬到院子裏曬曬太陽。
老人家年紀大了,但腦袋卻一點都不糊塗,看到這樣熱鬧的情景,心裏自然高興。
日子往好的方向奔着,家中後輩又孝順,前些日子還專門給她做了什麽山楂糕,說是有開胃健脾的功效。
山楂糕自然是管用的,但兒孫們的孝心也同樣重要。
一段時間下來,老人家的身體還真肉眼可見地康健了許多,面色也紅潤了不少。搞得王家兄弟幾個就差把謝虞琛當神仙供起來了。
他們倒是真有這方面的意思,想在家給謝虞琛立個神位。
無奈被許大郎及時發覺,攔住了他們。
但其實,王家兄弟并不是第一個有這種想法的,最先起了類似念頭的其實是攔住他們的許大郎本人。
許大郎雖然逢年過節也會去祭神,但心中多少存了些懷疑的念頭。
畢竟每日祭拜祈禱的人有那麽多,神怎麽可能全部都聽見?
日子該怎麽過還是得怎麽過。
直到遇見謝虞琛,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才真正品出點信仰神的味道來。
但偏偏他信仰的那個人卻不讓他信奉。
得知這件事的謝虞琛,卻沒有半點擁有了信徒的喜悅,一臉驚恐,大有一副許大郎敢供奉,他就敢自殺的樣子。
他既然占了大巫的名頭,自然也是專門了解過這方面的信息。
這個時代的信仰和他了解過的任何一種都不同,人們信仰天地,有天神和地神之說,而所謂“巫”則相當于天地之間的橋梁。
而且這個世界也沒有活人不能供奉的說法。畢竟在他們的認知裏,大巫就是溝通天地的存在,既是人,也兼具神的特性。
因此,許大郎說要供奉謝虞琛,那便是實打實要給他建神龛,立神位的。
謝虞琛想象了一下那個畫面:
他清早剛起床,正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往院子裏走,一轉身卻看到屋子的正中央擺着一張方桌。
香燭袅袅,上面赫然立着的是刻有他名字的神位。
旁邊還有許多他看不懂的神秘圖騰……
謝虞琛閉了閉眼,将腦海中的畫面驅逐出去,只覺得若是這樣他大概一步都不願踏出卧房門了。
斬釘截鐵地阻止了許大郎之後,見他仍有些不死心,謝虞琛深吸一口氣,決心徹底打消許大郎這可怕的念頭。
他給自己倒了杯熱茶,言辭懇切地從許大郎救下他開始說起,一直講到現在生意紅火的許家食肆。
不僅充分肯定了許大郎作為許家食肆的掌櫃,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并且還深刻強調了人主觀能動性的重要價值……
總之就一個意思:許大郎你能有現在的生意,是因為你踏實可靠,吃苦耐勞,聰明能幹,勤學好問。
就差把許大郎誇得天上地下獨此一份了。
所以如果他非要感謝一個人的話,就供奉他自己吧!
這一段話徹底把許大郎給說懵了,嘴巴張張合合,許久才找回自己的聲音。
他本想說若是沒有謝郎,他即使再努力也不會有現在的成就,但謝虞卻像是知曉他心中所想一樣,立馬說道:
“那你想想,如果碰到我的是錢家人,他們會救下我嗎?”
許大郎想了想錢母和錢父的為人,緩緩搖頭。
若是讓那家人遇見謝郎,別說會不會救人,不把謝郎身上值錢的東西搜羅一遍裝進自己口袋,就算他們良心發現。
“那若是他們學了做麥芽糖的手藝呢?能把生意做起來嗎?”
許大郎又搖頭。
當初蓬柳村的客舍生意那麽火,偏偏就錢家人賺不到錢。
又懶惰還又愛貪小便宜,做什麽生意都是做不成的。
“所以你看,即使他和你遇上同樣的情況,事情也會因為每個人的秉性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結果。”
其實他這一套話已經近乎詭辯。畢竟若是沒有謝虞琛,許大郎有可能還在為了生存苦苦掙紮,更不可能現在的成就。有了謝虞琛這個“因”,才會有許大郎後來的“果”,只能說二者缺一不可。
但謝虞琛的目的是打消給他立神位的念頭。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至于這些話許大郎能明白多少,又能做到哪一步,還是要看他自己。
就像他教給村人的明明是同樣的東西,但村裏人家的酸菜生意,就是有做得比其他人都好的。
在這些“做得比其他人好”當中,王家肯定算是其中一個。
靠着從許大郎那裏學來的腌菜手藝,再加上肯下功夫,王家這些時日賺了不少銀錢。
清點過數額後,王家二郎便和爺娘兄弟商量,看要不要再往家裏添幾個腌菜的壇子。
他們家有地窖,蘿蔔芥菜放在地窖裏一時半會兒壞不了,倒是不急。但謝郎說過這泡菜得在天冷時腌。若是天氣回暖,酸菜便容易壞。
倒不如趁着天氣合适多腌幾壇。左右他們與縣城中幾家食鋪簽了合同,肯定不愁賣。
王家爺娘想了想,也覺得是這個道理,便同意了二郎的提議,讓他領着兩個弟弟到燒窯的地方購置菜壇子去了。
但到了地方,他們卻意外遇上了一個不應該在這兒出現的人。
“二哥你看,那不是錢家大郎嗎?他們怎麽會在這兒?”王家三郎指着不遠處的一個人的背影道。
“好像還真是。”王二郎定了定神,朝着弟弟手指的方向看過去。
“那錢大郎怎麽會來這兒?”
不僅是王二郎,兄弟三個都有些疑惑。
“看方向像是從燒窯的那裏出來的。”王家二郎念叨了一句,帶着兩個弟弟進了窯廠。
這間小陶窯開在蓬柳村往南十來裏的一個村裏。
他們村西頭有座小山,山上的泥很适合用來燒陶,漸漸便發展起了燒陶的行當。附近村的人若是哪個缺陶鍋陶盆了,都會到他們村來買。
謝虞琛要定做泡菜壇子的時候,許大郎也是來這兒找人燒的。
當時許大郎問了好幾處燒窯的地方,人家都嫌那壇子做起來過于麻煩,什麽陶檐、內蓋外蓋的,還要緊密嚴實,賺不了幾個錢還平白耽誤他們功夫。因此都拒絕了許大郎。
最後只有一個姓林的匠人願意一試。也是他當時沒什麽生意,想着即使費些力氣,但能賺到錢就無妨。
誰知道就是這一試,幾個月後竟然給他帶去了那麽多的顧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