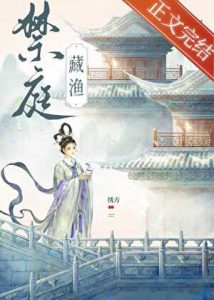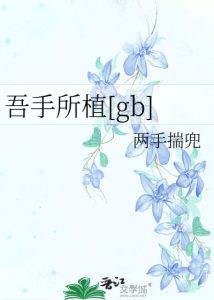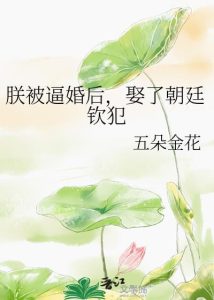他一下就哭了起來,眼淚嘩嘩地止也止不住,司馬遷慌了,邊替他擦着眼淚邊問怎麽了,他嗚嗚咽咽地說以前,父親也這樣摸他的頭,可是他死了,娘親不要我了。司馬遷沉默了會兒,說別哭,以後你跟着我吧。
後來他曾問,你為什麽收留我呀?
他笑着說,我那時一睜開眼,就看到又賊溜溜,又膽怯慌張的眼睛,還以為是只小狗呢,就當作小狗收留了,哪想還是只愛哭的小狗呢。
那年,他也剛剛加冠,為協助其父寫《史記》周游各地,他便跟着漫游江淮,到會稽、渡沅江、湘江,向背過汶水、泗水,于魯地觀禮,向南過薛、彭城,尋訪楚漢相争遺跡傳聞,過大梁,後回到長安,歷時五年。
五年間,他們被狼追過、被蛇咬過、被強盜綁過、爬過玄懸崖、趟過河流、吃過野菜……無論多艱難的時候,他都沒有丢下過他。
“怎麽此時回來了?”司馬遷的問話,拉回他的神志。
“衛将軍回京,我随之回來。”任安含糊地道,不願讓他知道與戰争相關的事,尤其是李陵事件。
去年秋,漢武帝命李廣利出征匈奴,李陵相輔,率五千名弓箭手行軍一月有餘,被匈奴三萬騎兵圍困,奮勇殺敵,逼退匈奴騎兵。匈奴單于急調八萬餘騎攻打李陵,李陵力挫匈奴,終因無後援而兵敗迫降。
朝臣譴責其貪生怕死,武帝問司馬遷,司馬遷認為李陵兵不滿五千,深入敵人的腹地,打擊數萬敵兵,雖然敗仗,亦殺敵無數,足以謝天下,不肯馬上去死,必有所圖,将來定會将功贖罪報答漢室。武帝認為他擔護李陵,貶低寵妃之兄李廣利,将其下獄。不久,傳來李陵帶兵攻打漢朝的消息,武帝殺李陵母親妻子,判司馬遷死刑。漢朝律法,死刑可以用金錢或是腐刑代替,司馬遷家裏貧寒,欲借款而人情寡薄,無人肯出手援助,只能受腐刑。
司馬遷沒再問什麽,讓他将案頭的竹簡拿來,支撐着要坐起來,舉動維艱。任安扶起他讓他靠在自己身上,“我讀給你聽。”他聲音清朗,讀書時從容舒徐,很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以往,他就這麽讀書給他聽,起初,是為了教他認字。那時,司馬遷每晚都會将白日的所見所聞刻在竹簡上,一個一個的教他認寫,他記性也好,每天能學會三字,三個月後就差不多能讀竹簡了,遇到些晦澀難懂的地方,就逐個的給他解釋,然後改成簡單易懂的句子。一年以後,他已經學會了很多字,司馬遷就讓他也試着寫見聞,等回到長安時,他已經能寫出很不錯的文章了。
但讀書給他聽已成了習慣,就在這個小院,或是明月清風的晚上,或是暗香浮動的黃昏,或是宿雨過後的早晨,從《詩》到《春秋》到《左傳》再到《離騷》,他布衣寒襟,揮卷灑墨,頗有上古之人的風流氣度。
可如今,卻變成這個樣子,只是說幾句公正的話,便遭如此毒手,天理何在?不禁悲憤交加。這時,領居已經請來的大夫,他到院中連吸了幾口氣,才平複心中怒火,卻不忍再視他那滿是傷痕的身子,躲在門外。
不久大夫就出來,對他說:“你父現在身體虛的很,揀幾劑藥給他吃,好生照顧。”嘆息着離開了。
司馬遷的妻子替他生了兩男一女,長子司馬觀,次子司馬臨,女兒已經出閣,妻子在司馬遷入獄之時,就帶着兒子改名換姓,逃到他鄉避難了。
他按大夫囑咐每日煎藥,精心伺候,一個月後,司馬遷身上普通傷口已好的七七八八,那種傷卻是回天乏術,他才三十五歲,後半輩子完全毀了。
次日,司馬遷便開始撰寫《史記》,五年游歷筆記起到關健作用,他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任安擔心他身體,每每想勸他休息會兒,話到嘴邊卻止住,因為知道,他忍受腐刑,就是為了寫《史記》,這是他痛苦的根源,也是唯一能減輕他痛苦的方法。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幫他整理數據,替他将文字刻在竹簡上,天冷的時候替他加件衣裳,在他困極伏案而睡時,将他抱到床上去。七尺男兒,瘦得只剩百來斤,骨頭硌着他的身子,鈍鈍地痛。
到清明節前,他的傷口已全部脫痂,這些天他沒有夜以繼日的寫《史記》,然精神卻愈發疲累,時常精神恍惚,冷汗濕衣。
任安知道根源所在,腐刑對于每個男人都是奇恥大辱,受人千秋诟病不說,更無顏面對父母,他又有何顏面去替祖宗掃墓?
這樣恍恍幾日,清明節那天,終還是提着香燭前去上墳,遠遠地看見墳前跪着的兩人,他眼睛頓時泛起了光彩,疾步過去,呼喚着兒子的名字。
兩人見着父親,先是大驚,問是人是鬼,接着臉色晦沉了下來,眼神閃爍,欲言又止。
父子相逢,尚未訴衷情,司馬遷便看到新成的墓碑,驀然僵住,任安随之看去,墓碑上寫着:先考司馬公遷之墓,怒極便要折了這碑,司馬臨攔住他,“不可!”
任安憤怒地道:“你父親未死,怎可立碑!”
兩人忽然就跪在司馬遷面前,痛哭悲訴:“古人雲: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最下腐刑極矣!今父親為茍活而受腐刑,辱及先人,辱及自身,亦……亦辱及孩兒和母親,倘若……”
“孩兒寧願父親英勇就死,甚過茍且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