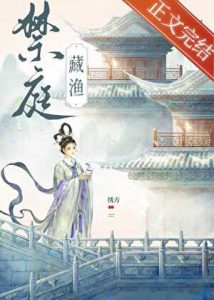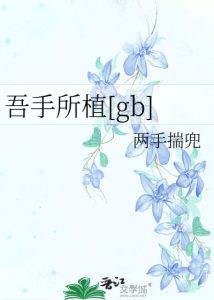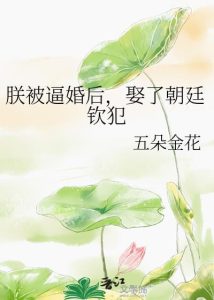第 25 章(三合一)
陳家每年固定在三月中祭祖, 繁文缛節無數,一整套下來少說也得十幾天。
這段時間裏,凡是陳家子孫, 一言一行都要受到拘束。若是放在從前, 陳汀還能靠裝病逃過一劫。
偏今年選了他們這一脈主持祭典, 他連躲都沒處躲。自早上一睜眼,幾個哥哥的目光就在他身上放着, 生怕他做出什麽出格的事來。
陳家傳承數代, 不知道散出去多少旁支,關系更是錯綜複雜。也虧得是陳府足夠大,才能招待得下這麽多親族。
若非要說這每年一次的祭祖還有什麽新鮮東西的話,那就只能是陳府新刷的牆面。
自那日陳父去了一趟陳汀的西院,見識到石灰砂漿的妙處後, 便同意了陳汀要将整個陳府的牆壁的都翻新一遍的提議, 并把這件事全權交給了陳汀處理。
半個月之後, 整個陳府大宅煥然一新。潔白平整的牆面, 光是看着就覺得十分舒心。
幾乎所有路過陳家大宅的人,都會被這抹紮眼的白給吸引, 駐足觀望一陣。遠道而來的陳家族人也不例外。
陳父對于親朋的誇贊和豔羨倒是表現得很冷靜,每每都會和人說——
“不算什麽新鮮東西,不過是我家六郎瞎鼓搗,讓人給家裏弄出來的罷了。”
但不知為什麽,明明是謙虛的話, 衆人就是從陳父那裏聽出了一點炫耀的滋味。
原本關注這陳父這一脈的陳家人就不少,再加上這段時間陳家确實沒少出風頭, 私底下談論的話也就漸漸多了起來。
從前許多人對陳汀都有幾分瞧不上,偶爾還會說些酸話, 像“雖然陳父将陳家經營得不錯,但在子孫的教養上啊,還是差點火候,你看那陳六郎,就不是個有出息的小輩”之類。
這大概是一種很奇怪的心态。好像只要證明陳父在教育子女上的失敗,他們就可以否定掉對方的成功;否認掉“陳父作為陳家的不起眼的一脈,卻能牢牢壓他們一頭”的事實;就可以讓他們心底那些隐秘的嫉妒和自卑,有一個順理成章的宣洩之處。
但現在,他們連這點可悲的自欺欺人也失去了——
原來他們一直看不上眼的陳六郎,說他不學無術,縱情聲色,是個扶不起的阿鬥雲雲。現在卻也做出了一番成績。
那什麽許家食肆的名聲遠在百裏之外的他們都有耳聞。食肆與陳家許多生意上的往來,都是由陳六郎一手負責。而就擺在衆人眼前的石灰砂漿,砌的牆看起來也是一等一的堅固美觀,估計過不了多久同樣會風靡開來。
想到這裏,衆人面上都帶了一點深意。若說從前的許家食肆還不夠惹眼,畢竟再多人吹捧也不過是幾口吃的,影響力實在有限。
但這石灰砂漿可不一樣。不論是從實用程度還是別的方面來看,只要運轉得當,未來簡直是不可限量。
若是他們也能跟着分一杯羹……
這些人能想明白的東西陳父心裏自然清楚,不然他也不會在專門在家族祭典上提起這件事。
之後的幾天裏,衆人對陳父的态度不免就變得複雜幾分。
有想要從他這裏探聽消息,好先人一步占領市場的;有好奇背後與陳父合作的那個人的;還有單純眼饞嫉妒的;簡直什麽人都有。
陳府中愈加微妙的氣氛陳汀當然也能感受到。他平日裏只是沒心沒肺了點,但又不傻。皺着眉琢磨了一會兒就想通了其中的彎彎繞繞,明白陳家這些變化幾乎都是因自己而起。
“阿書,你注意到沒有,今天我三伯父的臉色,啧啧,真難看啊。”
若說從前誰最看不上他,那一定非他這個堂伯父莫屬。從前這老頭就沒少當着衆人的面數落指責他。
今天他在前廳和幾個堂兄堂姐說話,本來話說得好好的,他那三堂伯非頂着一張尖酸刻薄的老臉過來挑他幾句刺,說他是沉迷奇技淫巧,将來不堪大用雲雲。
結果他話還沒說完,就有人主動過來和陳汀搭讪示好。
那人雖然看着年輕,在陳家的輩分卻比陳父還高一點,正打算翻新自家的府宅。看見陳府這樣氣派的裝潢,他自然是心動的厲害,便想問問這砂漿要如何配比,工匠從哪裏尋雲雲。
陳父這幾天正忙着祭祀的諸多事宜,他不好打擾,聽說這東西是陳汀讓人鼓搗出來的,便過來打聽打聽。
這樣的場景最近在陳府很是常見。比起素來威嚴的陳父,人們自然是更傾向于向那成天笑嘻嘻傻樂,沒什麽心眼的陳汀打交道。
他那三堂伯的臉色變了又變,從滿臉褶子的死老頭,便成了滿臉褶子黑臉死老頭,衣袖一揮氣沖沖地走了。
“真是……好久沒看到那老頭吃癟了。”陳家西院裏響起了陳汀幸災樂禍的聲音。
明天他們要上山祈福,難得今天能歇一天,陳汀毫不猶豫鑽回了自己的小院裏,再不肯露面。這幾天,因為石灰砂漿的事情,他幾乎成了所有人注意的焦點。
不論在哪都有人上前與和搭話。若說最開始他還有點沉迷于這種萬衆矚目的感覺,但沒過多久便覺出了其中苦痛,只恨自己不能擁有隐身的法術。
“還是七郎聰明。”
花廳裏,陳汀一邊低頭自欺欺人,假裝別人看不到自己,一邊思考起了陳淮,也就是他七弟的處世哲學。
小時候的陳七郎也是族中長輩重點關照的對象。八歲便能成詩,那是何等的天賦聰慧?
但不知從何時起,陳七郎身上的關注就越來越來少,偶爾有人想起,也只是嘆一句可惜便作罷。
從前陳汀不懂,明明他七弟天下第一聰明,為何要故意藏拙,平白被人同情嘲弄。要是他有那樣的學識,非得讓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不可。
但他現在算是明白過來,什麽稱贊吹捧都是虛的,能安安靜靜呆在自己屋裏,不被人打攪地烤一下午火才是世上頭等大事。
看他七弟,祭祖這麽些天,主動和他搭話的人一只手就數得出來。
這才是他夢寐以求的日子啊!陳汀只恨自己明白得太晚,現在只能硬着頭皮面對那些煩人的交際應酬。
正如衆人意料的那樣,石灰砂漿一面世就受到了人們的熱切追捧。城中富庶人家聚居的地方,白灰牆、青石瓦的府宅越來越多。進城的土路上,隔三差五就能看到農夫挑着擔子兜售和泥用的砂石。
石灰砂漿大受歡迎,最先受益的要數那些當初在許家做工的年輕人。
那些人家府上又不缺錢財,誰不想做領頭的那一批。要知道現在的江安府,堅固潔白的牆面不僅讓人看着舒心,更是成了一種潮流。
首先那石灰需要從北方運吧?能有這份閑錢說明他們家底豐厚;再其次能掌握砂漿的配比,還需要有門路、有人脈。
因着這幾個要素,在那些世家大族眼裏,最先擁有白牆已經成了某種象征,一個證明他們家族興旺鼎盛的标志。
需求遠大于供給,這就導致蓬柳村擁有技術的年輕人們立馬成為了香饽饽,那些富戶大家幾乎是在搶着雇他們做工。
第一次遇上這種場面的衆人顯然有些無措,幾乎是下意識地就找上了謝虞琛。
謝虞琛最初是不打算管這事兒的。他一直抱着的态度都是“我把技術教授給你,那這門手藝就是你的。後續能走到哪一步也都是看你自己,和他本人一點關系沒有。”
但看着面前的年輕人,一身補丁短打,雙手粗糙皲裂,不停揉搓着,因為冬天生了凍瘡,天氣回暖後就開始發癢。
身上滿是不屬于他們這個年紀的操勞留下的痕跡,但面上都是興奮的神色,其中還夾雜着一些被突如其來的機會砸中的茫然。
這是有可能改變他們命運的東西,謝虞琛心想。
不知為何,他突然有些心軟,最後還是沒将拒絕的話說出口,叫來許大郎把他們帶到前廳,在冊上記下衆人的姓名和能做工的時日。
有謝虞琛和許家食肆做後盾,替他們招攬工程,劃分安排工作,這些年輕人便不會像剛才那樣茫然無措,或因為沒有經驗生生錯過一個大好機遇。
做這件事對他本人自己好處寥寥,但謝虞琛還是做了,緣由不明。至于其它像砂石生産,水泥運輸的生意,也本着“不把錢賺盡”的原則沒有管過。
天氣日漸回暖,謝虞琛又把冬天收回去的躺椅給搬了出來。太陽溫暖和煦,躺在院裏依舊和去年秋天一樣舒服。
外面因為石灰砂漿而掀起的熱潮似乎一點都沒傳到他這兒,整個院子展現出一種“任外面紛擾喧嚣,我自安靜悠閑”的雅致,非常清新脫俗。
上午謝虞琛去前院看了一眼醬油的發酵情況。
一個月前,發酵好的大豆已經被清洗淨表面的黴菌,和鹽水一起倒進大缸,蓋上紗布開始晾曬。
曬醬選的是許家采光最好的地方,整整齊齊擺了三口大缸。不知道為什麽,每次路過這裏的時候,謝虞琛總會想到以前電視裏那句耳熟能詳的廣告詞。
“就在這兒曬,曬足一百八十……”
搞得他每次看到太陽底下的醬缸,就忍不住想笑。旁邊幹活的廚娘幫工們看得一頭霧水,還以為自己做了什麽惹人笑話的事。
後來到了淋醬的日子,謝虞琛找了一個三十公分長的竹簍直直插在醬缸中間。簍子上面的孔洞剛好是可以過濾掉豆子的尺寸。
醬汁源源不斷地滲進竹簍,又被人用瓢舀出去,均勻淋在豆子上。
如此反複幾十天後,醬缸裏的豆子慢慢開始融化破碎成顆粒狀,醬汁也逐漸從原本的土黃色便成了更深更濃的紅褐色,散發出醬油獨特的香氣。
光是聞着這個味道,謝虞琛就知道這幾缸醬油沒釀失敗。只等再接着曬上一個多月,讓醬油的風味更加濃郁後,就可以過濾裝壇。
過濾剩下的豆渣經過調味還能做成豆醬,用來炖菜或是做炸醬,味道都很不錯。
等待醬油釀好的日子裏,許家食肆的堂食也準備周全,第一批食客毫不意外,全是陳汀帶來的。
都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陳汀作為一個被謝虞琛親自蓋章認證的“吃貨”,他的那些朋友自然少不了幾個對美食的熱愛的人。
各式菜色一經上市,反響就很是熱烈。那些年輕郎君但凡嘗過一次許家食肆的菜色後,無一不是念念不忘地想吃第二遍,沒過幾天就拉着親朋好友,再次光臨了許家食肆。
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許家食肆的名頭很快便打了出去。
食肆的幾間客堂裏坐滿了食客。他們其中有的是慕名而來的生面孔,有的則是來了好幾次的熟客,專門帶着親眷過來吃飯的。
除了食客們自發的推廣以外,謝虞琛本人更是深谙營銷之道。什麽新客九折優惠,老客送一盒小吃之類的套路被他用得駕輕就熟,把顧客們拿捏得死死的。
不僅如此,謝虞琛還在大廳的牆上挂了幾個空白木牌。食肆每月逢九就會上新一道新菜品,菜名就寫在這空牌子上。
上新的通知一經公布,立馬就在食客群體中引起了小範圍的轟動。
首先便是因為食肆上新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縱觀整個江安府的大小酒樓食肆,還從未聽說有每月上新三道菜的地方。
食客們昂首期盼着新菜色的到來,每到逢九的日子,食肆的客堂總是人滿為患,早早就挂上了“客滿”的牌子。
連着推新了七八道新菜,眼看着大廳牆上的木牌就要挂不下了。這時,便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擔憂:若是按照食肆現在上新的速度,等到菜式越來越多,後廚忙不過來怎麽辦?
況且每道菜需要的食材也大不相同。這樣一家小小的鄉村食肆,怎麽可能一次備下那麽多種食材?
這樣一來,上新的菜式越多,舊的菜式豈不是就越有撤牌下架的風險。
衆人一聽,心道這個猜測有道理啊!從前他們只想着能吃到新菜品,卻忘了長期以往食肆根本承受不起那麽大的經營成本,到時候下架他們最喜歡的菜色怎麽辦?
常在食肆吃飯的顧客趕忙駕輕就熟地繞去後院,找來食肆的管事,向他們詢問起這件事。
得到的回答是:“下架一部分的舊菜式是肯定的,不然食肆很可能會虧本。至于下架哪些菜式,就要看郎君們的喜好了。”
大概就是根據顧客點某道菜的頻率排名,每月被點單最少幾個的菜品,下個月便會酌情考慮下架,換成其它菜式。
這話傳到食客們耳朵裏後,人們立馬加大了來許家食肆吃飯的頻率,每次吃飯一定要點自己最愛吃的那幾道菜。
一來是為了給自己喜歡的菜色提高點單量,二來也是怕這道菜下架之後便吃不着了,趕緊趁現在先吃個過瘾。
這一套組合拳下來,整個食肆的客流量不僅沒有随着時間的流逝日漸縮減,最後在某個既定的範圍內穩定下來,反而有越漲越高的趨勢。任誰見了不得說一句“謝郎好手段!”
許家食肆爆火幾個月,整個後廚衆人忙得腳不沾地,就連本來已經晉升成管理層的許大郎,都開始挽起袖子,重新幹起了颠勺的工作。
饒是如此,許家食肆的人手依舊不夠用,最後許大郎不得不從村裏招了許多手腳麻利的婦人娘子打下手。
光是做些洗菜燒水之類的雜活,每天就有十文錢的收入。這樣的好事誰見了不心動?
這就使得每次食肆招工的時候,後門的門檻都快被村人們踩爛了,要不是有人攔着,大家夥估計能為一個做工的名額大打出手。
原本食肆最大的那間正房是用來售賣糕餅豆幹一類方便運輸的吃食。但現在為了應對日漸增長的客流量,謝虞琛也不得不讓人把這間房給騰了出來,改成客堂。
至于原本擺在這裏的櫃臺和吃食,只能屈尊被搬去了前院南側的耳房裏,頗有一種“只見新人笑,哪聞舊人哭”的凄楚。
……
前往蓬柳村的路上,各式馬車行過,揚起陣陣塵土。
這些馬車裏坐着的大多都是去許家食肆吃飯的顧客。有的是三五關系熟稔的好友,相約一起打打牙祭;有的則是拖家帶口,一家老小都是許家食肆的忠實粉絲。
一輛馬車慢悠悠地行在路上,車裏傳來幾人說話的聲音。
“阿娘,你說許家食肆今天上新的菜品裏,會有和糖布丁一樣好吃的點心嗎?”坐在婦人懷裏的一個小姑娘,穿着青色的夾襖,擡起頭脆生生地問道。
糖布丁是許家食肆上個月上新的菜品,小姑娘吃過一次後就愛上了那軟乎乎甜津津的口感。
事實上糖布丁這樣的甜點也确實招小朋友喜歡。許多帶着小孩來的食客都會給孩子們點一份。
但坐在馬車裏的這個小姑娘年紀還小,她阿母擔心糖布丁這種甜食不便克化,每次便只允許她吃小半碗。
自上次吃糖布丁,到今天已經過去了七天,小姑娘早就饞了糖布丁的味道,自昨天便央着家中長輩再帶自己來一次許家食肆。
她雖然年紀不大,但心裏的“小算盤”打得可響啦!
今天是初十,阿母說許家食肆每逢初九便會上新一種新菜式。她們趕在今天來,自己兄長又最好新鮮,一定會讓父母點一份新菜式嘗嘗。
雖然她阿娘只允許她吃半碗糖布丁,但若是新出的菜式是像糖布丁一樣的甜食,她就又能吃一點,這樣四舍五入,她就吃了一整個的糖布丁啦!
想到這兒,小姑娘興奮地在阿娘懷裏晃了晃身子,望着馬車外不停後退的景色,小聲念叨:“我們什麽時候才能到蓬柳村啊,小寧和哥哥都要等不及啦!”
一旁坐着的小男孩聞言輕哼一聲,辯道:“我才沒有等不及呢!只有你。”
作為一個過了八歲生辰的小朋友,趙樂桓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大人了,不能再坐在阿娘阿爹的懷裏撒嬌,更不能像妹妹一樣,急着想去許家食肆吃飯。
他是男子漢,才不像妹妹一樣嘴饞。樂桓小朋友驕傲地揚起腦袋。
“你胡說,剛才我分明聽見你也咽口水了!”婦人懷裏的小姑娘鼓起腮幫子,大聲戳穿了自己哥哥。才不是只有她嘴饞呢!
“我沒有,是妹妹聽錯了。”
“你明明就有。”
“沒有!”
“就有!”
……
兩個小朋友在馬車裏吵吵鬧鬧的,一旁的婦人和夫君對視一眼,都露出了無奈的笑意。
直到馬車在許家食肆門前停下,兩個人都沒有吵出勝負。他們的父親張開雙臂,把兩個小朋友一左一右攬到自己懷裏,溫聲道:
“許家食肆已經到了,你們兩個人現在握手言和,阿爹就給你們每人都點一份糖布丁,怎麽樣?”
“好!那我還要點一個這回上新的菜。”有了糖布丁的誘惑,兩個小朋友很快便停止争吵,手拉手一起走進了許家食肆。
但讓小姑娘失望的是,這次上新的菜并不是和糖布丁一樣美味的甜點,而是一道叫炸醬面的主食。和索餅相比,他們家還是跟喜歡點一鍋粥飯或是幾張烙餅做主食,因為粥餅更适合配着各式炒菜吃。
而索餅就不一樣了,據食肆的小厮說,這叫作炸醬面的吃食是将索餅煮熟後,在上面澆一層肉醬,配上蔥絲、胡瓜絲一起拌着吃。
兩個小朋友對醬味濃郁,鹹香四溢的炸醬面興趣都不大,他們更喜歡甜香十足的糕點和酸辣爽口小菜。只有他們阿父聽完小厮的講解後,興致勃勃地給自己點了一碗。
炸醬面的醬自然是用釀醬油剩下的大豆醬做成的。肉則是選的雞肉,吃起來口感比肥瘦相間的豬五花是差了點。
但因為這段時間謝虞琛實在是太忙了,還沒來得及把養豬的計劃推行下去。還好,鹹香濃郁的豆醬足以彌補這一點小缺憾。
半個月前,在院子裏曬了幾個月的醬油終于釀好。過濾掉豆渣,在煮醬的時候,謝虞琛還專門從村人家中買了兩斤從山裏采來後曬幹的野山菇,放進醬油中一起煮沸。
和草菇一起煮過的醬油,比市面上的普通醬油更多一道鮮味。做飯的時候放一點進去,除了讓炒出來的菜顏色更加誘人以外,味道也更加豐富。
謝虞琛把釀好的醬油拿去廚房,庖廚們當即便做了一道醬油炒飯。
若是從前買來的醬油,廚師們必須小小心翼翼地使用才行。因為那種醬油的味道實在是太鹹,但凡加多了一點,就要面對整鍋菜都鹹得不能動筷子的結果。
但謝郎新拿來的草菇醬油卻不同,不僅沒有鹹得下不了嘴,而且還多了一分鮮甜的滋味。
廚師們只試用了一回,便徹底愛上了這個新醬油,原本那些又鹹又濃稠的醬油立馬被衆人“打入冷宮”,丢到角落裏落灰去了。
眼看着新醬油大受歡迎,謝虞琛當即便讓許大郎往家添了幾個醬缸回來,準備加大産量,繼續釀醬油。
這次釀好的醬油足夠廚房用個一年半載的,畢竟醬油這種東西放不壞,只要保存得當,甚至還會越放越香。
謝虞琛加大産量,一來是為了食肆日後用,二來則是打算把醬油和豆醬當成商品賣掉。
炸醬面做得很快,即使今天來食肆的食客中,十有八九都點了這道主食打算嘗嘗鮮,但也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鐘,一碗碗色澤誘人的炸醬面便從後廚端了出來。
前廳很快響起衆人吸溜面條的聲音,剛剛進店的那一家四口也不例外。
男主人很快就掌握了拌面條的手法,右手緊握筷子,手腕一提一翻,胡瓜蔥絲就均勻地落在了面條之間,被炸醬包裹起來。
熱騰騰的面條醬香十足,再配上清爽的胡瓜絲,一口吃下去,唇齒留香。
一碗炸醬面很快就見了底,男人意猶未盡地放下筷子,卻驚訝地發覺自己已經吃了個七八分飽,任由桌上的菜色有多誘人,他也再吃不下了。
看着妻子兒女呼嚕呼嚕吃得正香,男人遺憾地啧了一聲,摸了摸肚子,感嘆道:“這炸醬面雖然好吃,但未免太過頂飽,一碗面下肚都沒胃口吃其它菜,劃不來,劃不來。”
一旁的妻子聽了,也忍不住打趣道:“誰讓你吃那麽快?我都沒來得及說話,一個沒留神你碗就空了。”
男人讪笑一聲,小聲辯解道:“這不是那炸醬面太好吃了嘛。”
一旁端着托盤上菜的小厮聽到夫妻二人的對話,笑着插話道:“郎君若是喜歡炸醬面的味道,又擔心太占肚子,可以買一合豆醬回去自己在家做。”
“我們公子說了,這炸醬面好吃的關鍵就是上面醬的滋味,其餘的倒是不甚重要。”
“那這醬做起來可麻煩?”男人有些心動。
“一點都不麻煩,可簡單啦,我跟郎君講一遍做法,保準您能在家吃到一模一樣的味道。”小厮将托盤夾到胳膊下面,跟男人把炸醬的做法詳細說了一遍。
一旁的食客都豎着耳朵聽完了炸醬的做法,心裏的想法也大差不差:那小厮說得果然沒錯,好像這炸醬面确實不難做。
衆人心裏都盤算着,等他們一回家,就試着炒一回炸醬試試。若是真和今天吃過的味道相像,日後也不必為了一碗索餅大老遠跑這麽一趟。
許家食肆的炸醬面銷量平平,但百姓家中卻流行起了這種吃法。
就連官道上最不起眼的茶水鋪子,外面招攬顧客的布幡上都寫了一句類似“本店提供炸醬面”這樣的句子。
在城中做了一天工的人們回家的路上,也總會結伴到食肆裏,每人點一碗鹹香四溢冒着熱氣的炸醬面。
唏哩呼嚕地吃完,碗底剩下的那一層醬汁也不能浪費,問店家要一瓢煮過索餅的面湯泡着一并喝掉,一天的疲乏好像都被驅散了。
……
這幾個月許家食肆的生意有多紅火,衆人是看在眼裏的,陳汀更是感同身受。最開始他去許家食肆吃飯,不論什麽時候到,總能坐到最寬敞的那間包房裏。
但到後來,如果不是謝虞琛專門在不對外開放的後院給他留了一個房間,陳六郎和他的好友怕是只能在食肆外面支張木頭桌子吃飯,非常沒有“謝郎摯友”的排場。
饒是對許家食肆的生意有過一番了解,月初拿到賬本和分紅的陳汀還是驚住了。
沒有記錯的話,他只拿許家食肆的一成利吧?
怎麽比他們家兩個食鋪的總利潤加起來還多?
食肆剛開業時,店裏的食客有一大半都是陳汀帶來的,可以說是幫食肆掙了一個極好的開端;再加上陳家在食材采購上也幫了他們不少忙,謝虞琛便很大方地把食肆的利潤分給了陳汀一成。
确定自家的那兩間鋪子經營良好,近期沒有虧損的苗頭後,問題就只能出在許家食肆身上了。
許家食肆的利潤實在是太紮眼。一個開在鄉野的食肆,每月的利潤光是其中一成,就抵得上陳家兩間鋪子加起來的總利潤。還是開在定徐縣最好的地段,生意也算不錯的鋪子。
這得是什麽逆天的水平?陳汀不敢想象。
別說是陳汀,就連向來見多識廣的陳父也沒見過這樣的陣仗。
“許家食肆的生意……是真不錯。”再多的話陳父也說不出來,但他面上的表情足夠說明很多。
若說最開始,陳父還是抱着一種可有可無的心态,放任陳六郎與許家食肆來往,但現在他已經徹底把許家放在了心上。
許家食肆背後真正的主人不姓許,這件事陳父是清楚的。但對于謝虞琛本人,陳父了解得也并不多,只知道他姓謝,樣貌清俊,氣質不凡,再多的就探查不出來了。
那人好像是直接從哪裏冒出來似的,沒人知道他從何而來,在蓬柳村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村莊紮根又是為了什麽。
陳父自然不會相信陳汀那套“躲避仇家”的說法。那樣惹眼的樣貌,若真是有什麽仇家,不可能不用心遮掩。
當然,陳父也不可能想到,謝虞琛是從另一個世界穿越而來這樣離奇到話本都不會寫的劇情。
他思來想去,覺得這位謝郎要麽就是來自那些個鐘鳴鼎食的簪纓世家。那種世家大族向來不乏經世之才,但也少不得生出幾個禍害。難免就會有人為了利益,使些見不得人的腌臜手段。
這樣的人陳父自己族中就有幾個,想必那些大家族裏更是不少。
而按照自家六郎的描述,那位謝郎應當是個清雅灑脫的人物,說不定就是因為看不上那些卑劣龌龊之舉,不屑與其為伍才離開家族,跑來蓬柳村避世隐居。
陳父越想越覺得自己的推測有理,對謝虞琛的态度就更加重視。這其中除了有對謝虞琛背後家族的敬畏之外,多少還有些對他遭遇的不平。
陳父多次囑咐自家六郎,告訴他對待許家要謹慎周全。就是不知道陳汀本人聽進去沒有。
遠在蓬柳村的謝虞琛尚且不知陳父已經給他幻想出了一個顯赫尊貴又惹人憐惜的身世。
但不管他是被仇家追殺的小可憐,還是避世絕俗的貴公子,養豬的計劃是必須施行下去的,而且還要在夏收到來前就完成。
豬崽是謝虞琛從別村買回來的,因為這年頭養豬的人實在不多,買豬崽的時候還費了他不少力氣。
半大的小豬已經斷奶,因為謝虞琛怕路途颠簸給小豬的身體造成什麽不好的損傷,還專門讓接小豬的人雇了一輛牛車,下面墊上柔軟的稻草,小心翼翼地給拉了回來。
這待遇怕是比許多普通人出行的待遇都要好。但饒是如此,運回來的小豬也瘦了一圈,看起來沒什麽精神。
許家沒有給豬崽居住的豬舍,便花十文錢租下村人空着的一間草棚,把小豬暫養在那裏。
除此以外,謝虞琛還讓人用去油坊榨豆油剩的豆粕拌了麥麸和豬草,煮成粥飯一樣的豬食,涼冷了喂給小豬。
被雇來照看小豬的村人哪裏見過這樣的陣仗:趕路坐的是牛車,吃飯吃的是人煮好的食物,就連喝的水都是燒開了之後又晾冷的。
要不是聽說這些小豬長大之後就要殺了吃肉,他都想做只豬欄裏的小豬了。
但看着那些原本因為長途運輸消瘦不少的豬崽子沒過兩天就變得圓滾滾的,那些背地裏看笑話,或是覺得謝虞琛是在多此一舉的人又不得不閉嘴。
那些豬崽恢複健康後便被分別送到了村裏幾戶人家建好的豬圈裏。
這些人都是和謝虞琛簽訂過協定的。建豬圈的費用和養豬的飼料都從謝虞琛這裏出,但對方必須按照他的要求飼養小豬。
等到小豬長到了可以出欄的時候,謝虞琛便會按照約定分給那些人家豬肉。若是不想要豬肉的,也可以換成現銀或是糧食。
這幾乎是一項無本的生意,除了要承擔一項“把豬養死後需照價賠償”的風險。但比起豐厚的利潤,這項風險也變得十分微不足道起來。
村裏人家誰還沒養過牲畜?更何況謝虞琛協定上列出來的養豬方法又那麽詳細。
什麽五天打掃一次豬圈,早晚檢查小豬的進食情況之類的,就是天上的仙豬來了,他們都能給養得圓圓胖胖的。
這樣的念頭一生出來,村人們對于一件新鮮事物的畏懼便消減了大半。更何況自去年秋天許家食肆開起來之後,村人們跟着許家做的生意沒有一個不是賺得盆滿缽滿,沒道理到了他們這裏,養幾只豬就恰巧會遇上失敗。
給自己打了幾劑強心針的村人們很快便與許大郎簽下了協議,帶着自家認養的豬崽子回去了。
許家要與人合作養豬的消息很快便傳到村人耳中,許多人更是跑到認養了豬的人家那裏,想看看那豬崽子是怎樣的一個養法。
這些人裏,一部分是空不出人手來侍弄豬崽,所以沒和許家簽訂協議的。另一部分人則是有意向與許家合作,但是還不太能下定決心,所以計劃觀望一陣。
謝虞琛倒也沒讓人藏着掖着那養豬的法子,他不靠養豬發財,單純是需要豬肉做菜而已。
若是有更多的村人養豬,對他而言反而更方便,許家食肆需要豬肉的時候直接找村人購買就行。
不過這估計得是這一茬豬長大以後的事了。畢竟人們得看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才可能下定決心養豬。
但不管怎樣,許家要養豬的事情已經在蓬柳村傳開。“許家的豬過得都比人好”也成了這幾天村人常說的話。
現在的許家食肆,收入來源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正紅火的堂食生意;另一部分便是來自那些販賣給貨郎的,方便運輸的熟食。
本來後一部分是有些冷清下來的,謝虞琛甚至還想過要不幹脆取消這一部分,省下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堂食中去。
最後還是考慮到有許多以販賣食肆吃食為生的貨郎,貿然取締怕是會影響了這些人的生計,謝虞琛才打消這一念頭。
結果等到炸醬面一出,許多食客離開食肆的時候都捎帶買了些豆醬,回去一嘗,果然和店裏做的一樣美味,後來更是開發出許多新吃法。
豆醬便這樣火了起來,連帶着原本有些冷清的熟食生意也重新翻紅了一把。
謝虞琛便把這一部分徹底定位成了類似小雜貨店一樣的存在。不管琢磨出什麽新鮮東西,都往那間小屋子裏一擱。
有些吃飽喝足的食客便會順便進去逛逛,若是看上什麽東西,就買回來帶到家裏去。
偶爾也能掀起一陣浪潮,比如那個做飯很好用的鍋鏟和笊籬。
除了食肆和已經成為雜貨鋪的耳房,謝虞琛近期并不打算琢磨什麽新的東西。主要是現有的生意已經接近許家這間小院能承擔的最大限度。
而且雖然謝虞琛在外人面前表現得非常游刃有餘、成竹在胸,但實際上……啧,這其實是他第一次接觸和養豬有關的事情。
謝虞琛懸着心,時不時便要問問農戶們豬崽的情況,實在是沒有精力再操心別的事情。
很快,便到了他養豬計劃裏第一個要邁過的大檻——劁豬。